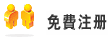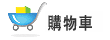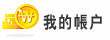| | | | 加西亞·馬爾克斯作品集(共14冊) | | 該商品所屬分類:其他分類 -> 圖書新品 | | 【市場價】 | 3563-5164元 | | 【優惠價】 | 2227-3228元 | | 【介質】 | book | | 【ISBN】 | 9787544278805 | | 【折扣說明】 | 一次購物滿999元台幣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2000元台幣95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3000元台幣92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4000元台幣88折+免運費+贈品
| | 【本期贈品】 | ①優質無紡布環保袋,做工棒!②品牌簽字筆 ③品牌手帕紙巾
|
|
| 版本 | 正版全新電子版PDF檔 | | 您已选择: | 正版全新 | 溫馨提示:如果有多種選項,請先選擇再點擊加入購物車。*. 電子圖書價格是0.69折,例如了得網價格是100元,電子書pdf的價格則是69元。
*. 購買電子書不支持貨到付款,購買時選擇atm或者超商、PayPal付款。付款後1-24小時內通過郵件傳輸給您。
*. 如果收到的電子書不滿意,可以聯絡我們退款。謝謝。 | | | |
| | 內容介紹 | |

-
出版社:南海
-
ISBN:9787544278805
-
作者:(哥倫比亞)加西亞·馬爾克斯|譯者:陶玉平
-
出版日期:2015-09-01
-
包裝:平裝
-
開本:其他
-
版次:1
-
印次:1
-
★ 馬爾克斯四大經典短篇小說集之一,魔性與靈**織的傑作!
★ 他們在時間裡迷了路,他們為失去了的世界哭泣。
★ 馬爾克斯的14種孤獨,夢境中,困境中,恐懼中,欲望中,溝通中……
★ 關於對失去了的世界的回憶;關於不同處境下個人的孤獨。
★ 收錄《藍狗的眼睛》《六點鐘到達的女人》《有人弄亂了這些玫瑰》《伊莎貝爾在馬孔多觀雨時的獨白》等名篇
★ 翻開本書,不一定能找回每個人失去了的時光,但能夠獲得一種全新的觀看已逝世界的方式,獲得和歲月角力的可能。
-
短篇作品集《藍狗的眼睛》共收錄加西亞·馬爾
克斯20-28歲期間創作的14篇短篇小說。本書出版後
,在拉美地區引發了閱讀狂潮。這些故事講述的是同
停滯的時間一起停滯的人物與現實。既有作者對故鄉
的追憶、對童年經歷的再現,也有他對孤獨、死亡、
荒誕、永恆等主題的探索。
《藍狗的眼睛》內容簡介:《藍狗的眼睛》所收錄的是馬爾克斯前期的短篇小說,包括《第三次忍受》《三個夢遊者的苦痛》《藍狗的眼睛》《六點鐘到達的女人》《有人弄亂了這些玫瑰》《納沃,讓天使們等候的黑人》《有人從雨中來》《伊莎貝爾在馬孔多觀雨時的獨白》等14篇經典。
《第三次忍受》是馬爾克斯看完《變形記》的第二天一氣呵成寫下的。這篇小說由國家日報《觀察家報》發表,占了六大豎版的版面。在國家的大報紙上首次發表小說,標志著年僅20歲的馬爾克斯正式步入了哥倫比亞的文學殿堂。
《六點鐘到達的女人》是馬爾克斯和朋友打賭之後寫下的作品,賭他寫不寫得了偵探小說;這篇小說是馬爾克斯創作生涯中最優秀的作品之一。《有人弄亂了這些玫瑰》的主人公形像則來自童年時期外祖母夜晚講的恐怖故事;在這篇小說中,死亡不再隻是一種苦難……
這些故事講述的是同停滯的時間一起停滯的人物與現實。既有作者對故鄉的追憶、對童年經歷的再現,也有他對孤獨、死亡、荒誕、永恆等主題的探索。
-
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27年出生於哥倫比亞馬格達萊納海濱小鎮阿拉卡塔卡。童年與外祖父母一起生活。1936年隨父母遷居蘇克雷。1947年考入波哥大國立大學。1948年因內戰輟學,進入報界。五十年代開始出版文學作品。六十年代初移居墨西哥。1967年《百年孤獨》問世。1974年出版《藍狗的眼睛》。198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2014年4月17日於墨西哥病逝。
-
第三次忍受
埃娃在貓身體裡面
突巴耳加音煉星記
死神的另一根肋骨
鏡子的對話
三個夢遊者的苦痛
關於納塔納埃爾如何做客的故事
藍狗的眼睛
六點鐘到達的女人
石鸻鳥之夜
有人弄亂了這些玫瑰
納沃,讓天使們等候的黑人
有人從雨中來
伊莎貝爾在馬孔多觀雨時的獨白
-
六點鐘到達的女人
彈簧門開了。這個時候何塞的飯館裡是沒人的。時鐘剛剛打過六點鐘,他知道,通常隻有到了六點半老主顧們纔會來。他的顧客就是這麼保守,中規中矩。可時鐘剛打完第六下,和每天這個時候一樣,進來了一個女人,她一言不發,坐在高高的旋轉椅上,雙唇之間還叼著一根沒點燃的香煙。
“你好,女王。”何塞看見她坐下來,先和她打了個招呼。然後走向櫃臺另一頭,用一塊干抹布擦拭著玻璃臺面。隻要有人走進飯館,何塞總會做這同一個動作。盡管和這個女人已經相當熟了,金紅頭發的胖店主還是表現出一個勤勉男人的日常做派。他在櫃臺另一頭開了腔。
“**想要點兒什麼?”他招呼道。
“我想先教教你怎麼做個紳士。”女人說。她坐在一排旋轉椅的盡頭,雙肘支在櫃臺上,嘴裡叼著根沒點火的香煙。說話時她的嘴巴咬得緊緊的,好讓何塞看見她那根沒點著的煙。
“剛纔我沒瞧見。”何塞說。
“你還是什麼都瞧不見。”女人說道。
何塞把抹布放在櫃臺上,走到黑乎乎的、散發著一股柏油和髒木頭味兒的櫃櫥跟前,片刻之後,他回來了,手裡拿著火柴。女人彎下腰來,為的是夠著男人那毛茸茸的、粗壯的手裡的火。何塞看見那女人一頭蓬松的頭發塗抹著厚厚一層廉價頭油,看見她繡花緊身胸衣上方裸露的肩膀。他還看見了那女人軟塌塌的胸脯,正在這時,女人抬起頭來,嘴上的煙已經點燃了。
“你**真漂亮,女王。”何塞說。
“別說蠢話了,”女人告訴他,“別以為這樣我就會給你付賬。”
“我想說的不是這個意思,女王,”何塞又說道,“我敢打賭,你**的午飯把肚子喫壞了。”
女人吞下**口濃濃的煙霧,雙手交叉,胳膊肘還是沒離開櫃臺,透過飯館寬大的玻璃,朝街上望著。她神情憂郁,憂郁中帶著厭煩和粗鄙。
“我去給你煎塊上好的牛排。”何塞說。
“我可沒錢。”女人說。
“這三個月你從來就沒有過錢,可我總是給你做好喫的。”何塞說道。
“**不一樣哦。”女人說這話時神情陰郁,眼睛還是看著街上。
“每**都一樣,”何塞說,“每天時鐘指到六點,你就會進來,說你餓得像條狗一樣,然後我就會給你做點兒什麼好喫的。**的區別就是,**你沒說自己餓得像條狗,而是說了句**不一樣。”
“沒錯。”女人說著轉過身來,看著櫃臺另一邊正在查看冰箱的男人。她盯住他看了兩三秒鐘,然後又看了看櫃櫥上方的鐘。六點零三分了。“沒錯,何塞。**是不太 那噪音又響起來了。那是一種冰冷、鋒利、硬邦
邦的噪音,他早就十分熟悉,隻是此刻它變得尖利而
傷人,仿佛一夜之間他已經無法適應它。
那噪音在他空空蕩蕩的頭顱裡回旋著,悶悶的,
帶著刺。他的腦殼四壁之間就像建起了一座蜂房。聲
音越來越大,一圈一圈,連綿不斷,從裡面敲擊、震
動著他的椎骨,與他身體固有的節奏極不合拍,極不
協調。作為一個實在的人,他的機體結構一定是出了
什麼問題,一定有一樣什麼東西,“從前”運轉得挺
正常,而現在卻像有一隻瘦骨嶙峋的手從裡面一下一
下猛烈地、重重地敲擊著他的頭,讓他一生所有的痛
苦感覺都湧上心頭。他有一種動物本能的衝動,想把
拳頭捏緊,壓在因*望痛苦而青筋暴起的太陽穴上。
他真想用兩隻感覺靈敏的手掌找出那尖利如金剛石般
的鑽透他的噪音。他想像著自己在燒得滾燙的腦袋中
的一個個角落裡搜尋那噪音,臉上露出了家貓般的表
情。差一點兒就要捉住它了,可是沒能成功。那噪音
長著光滑的皮膚,幾乎無法捉住。可他下定決心,一
定要用自己練就的嫻熟本領捉住它,並*終以發乎*
望的全部力氣將它久久地捏在手心。他*不能讓它再
跑進耳朵裡去,他要讓它從自己的嘴巴裡、從每一個
毛孔裡,或是從眼睛裡跑出去,哪怕雙眼在噪音跑過
時凸起甚至瞎掉,他也要從那破碎的黑暗深處看著那
噪音離開。他*不允許它再在自己的頭顱內壁揉搓它
那些碎玻璃或是冰凍的星星。那噪音確實如此:就像
把一個小孩的頭往混凝土牆上無休無止地撞擊,又像
大自然中一切堅硬物體猛烈撞擊的聲音。可是,隻要
能把它圈住,把它隔離開來,就可以不再受它的折磨
。當然還要把那個變幻莫測的家伙在它自己的影子裡
砍成碎片,抓住它,*終牢牢地捏緊它,用盡全身力
氣把它摔到地面上,還要狠狠地踩它幾腳,直到它一
動不動,直到這時,纔可以喘著氣說,這個一直折磨
著他、讓他發狂的噪音,現在終於被他殺死了,它現
在躺在地面上,就像任何一件普通的東西一樣,死得
透透的。
然而他實在沒辦法壓住自己的太陽穴。他的雙臂
變得很短,這會兒就像是侏儒的手臂,又短又粗又胖
。他努力想搖一搖頭。頭一搖,那又大又木的腦袋裡
噪音響得*厲害了,腦袋隨著一股越發巨大的力量向
下墜去。那噪音沉重而堅硬,如此沉重而堅硬,剛纔
倘若捉住並摧毀了它,他一定會有一種將一朵用鉛塊
打成的花朵一瓣一瓣撕下來的感覺。
這種噪音他“從前”也聽到過,向來如此揮之不
去。比方說在他**次死去的那**,他就聽到過。
那是在面對一具尸體的時候,他明白了那其實是他自
己的尸體。他看著自己的尸體,還摸了摸,感到自己
無可觸摸,無體無形,根本就不存在。他真真實實是
一具尸體,而且正正經經由自己年輕多病的軀體體驗
著死神的來臨。整間屋子裡空氣都凝固了,就像是填
滿了水泥,水泥塊裡,各樣東西依然像在空氣中那樣
一樣。”說完,她吐出一口煙霧,接著說了下去,話又短又充滿了感情,“**我可不是六點鐘來的,所以不一樣,何塞。”
何塞看了看鐘。
“要是這個鐘慢一分鐘的話,我就砍下自己一隻胳膊給你。”他說。
“不是說這個,何塞。我是說,我**不是六點鐘來的,”女人說道,“我來的時候差一刻六點。”
“女王,這鐘剛打過六點,”何塞說,“你進門的時候剛剛打過六點。”
“我在這裡已經待一刻鐘了。”女人說。
何塞走到女人跟前,一張紅肜肜的大臉一直伸到女人面前,又用食指拉了拉自己的眼皮,說:
“朝我這兒吹口氣。”
女人頭向後仰躲著,她一臉正經,有點兒生氣,溫柔纖弱,在一層憂傷和疲倦的薄霧籠罩下,變得*漂亮了。
“別說蠢話了,何塞。你知道的,我這六個多月滴酒未沾。”
男人微微一笑。
“這話你對別人說可以,”他說,“跟我就別來這一套了。我敢打賭,你們兩個人至少喝了二斤。”
“我隻不過和一個朋友喝了兩口。”女人說。
“哦,這一說我就明白了。”何塞說道。
“沒什麼需要你明白的,”女人又說道,“反正我已經在這裡待了一刻鐘。”
何塞聳了聳肩。
“好吧好吧,要是你願意的話,就算你在這裡待了一刻鐘,”他說,“不管怎麼說,早十分鐘晚十分鐘又有什麼要緊呢。”
“當然要緊,何塞。”女人說完把兩隻胳膊平平地伸在櫃臺的玻璃臺面上,帶著漫不經心的神情,懶洋洋的。她說:“不是我願意不願意,我就是來了有一刻鐘了。”說著她又看了看鐘,改口說道:“我說什麼呢,我已經來了二十分鐘了。”
“都行,女王,”何塞說道,“隻要看見你高興,我把**一夜送給你都沒問題。”
在整個這段時間裡,何塞一直在櫃臺後忙個不停,把東西挪挪位置,把某件東西拿開再放到別的地方。他干著自己該干的事。
“我想看見你高興。”他又重說了一遍,然後突然停住,轉向那個女人:“你知道我很愛你嗎?”
女人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是—嗎?真是看不出來,何塞。就算你有一百萬比索,你覺得我會為了這個和你在一起嗎?”
“我不是這意思,女王,”何塞說道,“我再跟你打一次賭,你中午飯肯定喫壞了。”
“我說這話可不是因為這個,”女人說,她聲音裡冷冷的勁頭少了一點兒,“是因為沒有一個女人受得了你,哪怕是為了一百萬比索。”
何塞臉一下子紅了。他背對著女人,開始撢櫃櫥裡瓶子上的灰塵,說話時連頭都沒回排列著,他就在那裡,在這一整塊東西裡,被小心翼
翼地安放在一口僵硬卻又透明的水泥棺材裡。那一次
,他的頭腦裡也響著“那種噪音”。他的腳底板遙遠
而冰涼,在棺材另一端,人們放了一個枕頭,因為那
時棺材對他來說太大了,不得不做點兒調整,好讓尸
體適應它新的也是*後的歸宿。人們給他裹上一襲白
衣,又給他的頜骨繫上一塊手帕。他就穿著這樣一身
壽衣,感覺挺美,死得挺美。
P3-5
。
“你**真讓人受不了,女王。我看你*好把牛排一喫,然後回去睡覺。”
“我不餓呀。”女人說完,又看著街道,看著傍晚時分城裡亂哄哄的行人。有那麼一會兒,飯館裡安靜得有點兒古怪,隻有何塞收拾櫃櫥的響聲不時打斷這寧靜。突然,女人把目光從街上收了回來,又開了腔,這回她的聲音壓得低低的,柔柔的,聲音也不一樣了。
“你是真的愛我嗎,小佩佩?”
“是真的。”何塞悶悶地答道,沒有看她。
“連我剛纔對你說那樣的話也不在乎嗎?”女人追問道。
“你剛纔說什麼了?”何塞的嗓音還是悶悶的,沒有看她。
“就是一百萬比索那句話。”女人說。
“那話我早忘了。”何塞說。
“那就是說,你愛我?”女人又說。
“是的。”何塞回應道。
談話到這兒停了下來。何塞還是臉朝著櫃櫥,忙來忙去,還是看也不看那女人一眼。女人又噴出一口煙霧,把胸脯抵在櫃臺上,然後,帶著點狡黠和淘氣,講話前咬著舌頭,話說出來像刀子:
“哪怕我不跟你上床嗎?”她問道。
直到這時,何塞纔又看了她一眼。
“我愛你愛到了不會跟你上床的地步。”他說。然後他走到她跟前,面對面看著她,強有力的雙臂支撐在她面前的櫃臺上。他直視著她的眼睛,說道:“我愛你愛到了每天下午都想把帶你走的男人殺死的地步。”
一瞬間,那女人看上去有點兒困惑。接著,她用心看了看這個男人,目光裡半是同情,半是嘲弄;接下來又有一刻的茫然,沒有說話;*後她放聲大笑起來。
“你喫醋了,何塞。太棒了,你喫醋了!”
何塞臉又紅了,帶著明顯的局促不安,幾乎有點兒無地自容,就像一個孩子一下子被人揭穿了所有的秘密。他說:
“**下午跟你說什麼你都聽不明白,女王。”他用抹布擦了擦汗,又說道,“這不像話的生活已經把你變成個粗野的人了。”
可是這會兒那女人的表情又變了個樣。
“那就是說你沒有嘍。”她說。
她又看著他的眼睛,目光裡閃動著奇異的光,像是憂傷,又像是挑戰。
“那就是說你沒喫醋嘍。”
“一定意義上說,我是喫醋了,可並不像你說的那樣。”
他松了松衣領,又擦了擦汗,用抹布擦著脖子。
“那麼到底是什麼樣?”女人追問著。
“是我太愛你了,不想看見你干這種勾當。”何塞說。
“什麼勾當?”女人問。
“就是每天換一個男人帶你走。”何塞說道。
“你真的會為了不讓這種男人帶我走就把他殺掉嗎?”女人問道。
“不是不讓他走,”何塞說,“我殺他是因為他帶著你走。”
“還不都是一回事兒嘛。”女人說。
談話的刺激味兒越來越濃了。女人壓低了嗓音,聲音甜甜的,著了迷似的。她的臉幾乎貼在了那男人健康平和的臉上,男人一動不動,仿佛被她說話的氣息迷住了一般。
“我說的都是實話。”何塞說。
“照這樣說,”女人說著伸出一隻手撫摸著男人粗壯的胳膊,另一隻手扔掉了煙頭,“……照這樣說,你是能殺人的嘍?”
“為了我剛纔說的那種事,我能。”何塞說著,嗓音變得悲壯起來。
女人笑得花枝亂顫,絲毫不想掩飾嘲弄的意思。
有人弄亂了這些玫瑰
**是星期天,雨也停了下來,所以我打算帶上一束玫瑰去給自己上墳。玫瑰花紅白相間,是她種了用來獻給祭壇或編成花冠的。鼕天裡天氣悶悶的,有點怕人,一上午都陰沉沉的,使我想起了村裡人丟棄死人的那個山崗。那裡光禿禿的,一棵樹也沒有,風吹過之後,星星點點灑落著一些老天爺施舍的殘渣。現在雨停了,中午時分的陽光應該已經把山坡上的泥地曬干了,我可以走到墳頭,那底下躺著我孩提時的軀殼,隻是現在已經在蝸牛和草根之間變成了一堆雜亂的零碎。
她跪在她那些聖像跟前。我想去祭壇前把那幾朵*紅*鮮的玫瑰拿到手,但**次沒能成功,之後我就一直在屋裡沒挪動地方,而她一直神思恍惚。原本我**可能已經得手了;可是燈突然閃了一下,她從恍惚中驚醒,抬起頭,向放著椅子的角落看了一眼。她一定在想:“又是風。”因為祭壇那邊果真有什麼東西響了一下,房間晃動了一下,仿佛那些滯留在她身上的回憶被觸動了一般。那時我明白了,我還得再等下一次機會纔能去取那幾朵玫瑰,因
為她這會兒頭腦清醒,而且正看著那把椅子,我如果把手伸到她臉旁,她會感覺到的。現在我能做的就是等她過一會兒離開房間,去隔壁房間睡她那星期天的例行午覺。那時,我就可以趁她還沒回這個房間、死死盯住那把椅子之前,帶上我的玫瑰離開。
上個星期天事情要難辦一些。我足足等了快兩個小時她纔進入沉醉的狀態。那天,她看上去煩躁不安,仿佛一直被某個確定的念頭折磨著:她在這屋裡的孤獨感突然間減退了。她拿著一束玫瑰在屋裡轉了好幾圈,*後纔把它們放在了祭壇前面。然後她走到過道,又轉進屋子,向隔壁房間走去。我知道她在找那盞燈。後來當她又走到門口的時候,在走廊的光影裡,我看見她身上穿著深色外套,腿上是粉色長襪,我感覺她還像四十年前的那個小女孩一樣。那時,就在這間屋子裡,她在我床前低下身來,對我說:“現在您的眼睛又大又僵,是他們用小棍兒給支開的。”那是在八月裡的一個遙遠的下午,一群女人把她帶到這間屋子裡,給她看了尸體,對她說:“哭吧。他就像你的哥哥一樣。”而她,就那樣靠在牆上,哭著,很聽話,身上仍舊濕漉漉的,那是被雨水打濕的。
三四個星期天過去了,我一直琢磨著怎麼纔能接近那些玫瑰花,可她一直守在祭壇前,守著它們,那股機靈勁兒令人喫驚,她在這屋裡生活了二十年,我從未發現她如此警覺。上個星期天,她出去找燈的時候,我總算選準了幾枝特別棒的玫瑰花。我從來沒有離實現自己的願望這麼近過。可就在我打算回到椅子旁的時候,我聽見過道裡傳來了腳步聲,我匆匆忙忙地把祭壇上的花弄整齊,就看見她出現在門口,手裡舉著一盞燈。
她身上穿著深色外套,腿上是粉色長襪,然而她臉上閃現出某種像顯靈的亮光。這時的她不像是那個二十年來一直在院子裡種玫瑰的女人,而像是那個八月裡被人們帶去隔壁屋裡換衣服的女孩,四十年過去了,她變胖了,也變老了,現在回到這裡,手裡舉著一盞燈。
雖說在熄滅了的爐子旁烘了二十年,我鞋上那天下午結的泥巴的硬殼還在。**,我去找鞋,那時大門已經關上了,門檻那兒的面包和一束蘆荟已被取走,家具也都搬走了。所有的家具都搬走了,隻留下角落裡那把椅子,正因為有了這把椅子,我纔得以度過之後的歲月。我還知道人們把那雙鞋放在那裡是為了烘干它們,而他們從這所房子裡搬走的時候,根本就沒人記起它們。所以我纔去找我的鞋。
許多年之後,她回來了。已經過去了那麼久,屋子裡麝香的氣味早已和塵土味,和干巴巴的、若有若無的蟲子味渾然一體。我一個人待在屋裡,坐在角落那兒,等候著。我已經學會了辨別木頭腐爛時發出的聲音,辨別緊閉的臥房裡陳舊空氣的鼓翼聲。她就是這個時候來的。她站在門口,手裡提著一隻箱子,戴了頂綠色的帽子,身上穿著那件從那時起再沒離過身的棉布上衣。那時她還年輕,還沒有發胖,長襪裡裹著的小腿也不像現在這麼粗。她打開房門的時候,我渾身是土,結滿了蜘蛛網,在屋子裡某個地方叫了二十年的蛐蛐也靜了下來。可盡管如此,盡管有塵土和蜘蛛網,盡管那隻蛐蛐突然改變了主意,也盡管剛到的她年齡上
有了變化,我還是認出了她,她就是八月裡那個大雨傾盆的下午陪我一起在馬廄裡掏鳥窩的女孩。她現在的樣子,站在門口,手裡拎著箱子,頭上戴著頂綠色的帽子,仿佛馬上就要尖叫,馬上就要說出當時說過的話:那是在人們發現我仰面朝天摔在馬廄的草堆裡,手裡還緊緊握著一節折斷了的梯子橫杠的時候。她把門**打開後,合頁發出了嘎吱聲,屋頂上的灰土稀稀拉拉地落了下來,仿佛有人用錘子敲打著房梁。這時,她在門口的光影中遲疑了一下,然後把半個身子探進房間,說了句話,那聲音就像在喚醒一個沉睡的人:“孩子!孩子!”而我一直靜靜地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