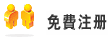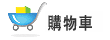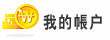| | | | 幸福(曼殊斐爾小說集) | | 該商品所屬分類:小說 -> 作品集 | | 【市場價】 | 201-291元 | | 【優惠價】 | 126-182元 | | 【介質】 | book | | 【ISBN】 | 9787538740851 | | 【折扣說明】 | 一次購物滿999元台幣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2000元台幣95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3000元台幣92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4000元台幣88折+免運費+贈品
| | 【本期贈品】 | ①優質無紡布環保袋,做工棒!②品牌簽字筆 ③品牌手帕紙巾
|
|
| 版本 | 正版全新電子版PDF檔 | | 您已选择: | 正版全新 | 溫馨提示:如果有多種選項,請先選擇再點擊加入購物車。*. 電子圖書價格是0.69折,例如了得網價格是100元,電子書pdf的價格則是69元。
*. 購買電子書不支持貨到付款,購買時選擇atm或者超商、PayPal付款。付款後1-24小時內通過郵件傳輸給您。
*. 如果收到的電子書不滿意,可以聯絡我們退款。謝謝。 | | | |
| | 內容介紹 | |

-
出版社:時代文藝
-
ISBN:9787538740851
-
作者:(英)曼殊斐爾|譯者:徐志摩
-
頁數:232
-
出版日期:2012-09-01
-
印刷日期:2012-09-01
-
包裝:平裝
-
開本:20開
-
版次:1
-
印次:1
-
字數:134千字
-
《幸福:曼殊斐爾小說集》是英國作家曼殊斐爾的經典短篇小說選集,亦是新西蘭文學花園的孔雀開屏之作。
在徐志摩的眼裡,曼殊斐爾其實是一座令他神魂顛倒的維納斯偶像,是一位不容褻瀆的藝術女神。那美麗女人的身上,寄托著他那“愛、自由、美”的理想。
英語寫作教科書式的小說作品,多位翻譯大師追捧的典範文本,其中含有收入牛津大學版英語教材的《園會》、《一杯茶》。
中英對照,****雙語合璧版本,精彩演繹曼殊斐爾的傑作。
-
《幸福:曼殊斐爾小說集》是曼殊斐爾創作的短篇小說選集,共收錄了
曼殊斐爾的代表作《幸福》、《園會》等短篇小說8篇,還附錄了徐志摩悼
念她的文章和詩歌。曼殊斐爾在藝術上深受契訶夫的啟發,不設奇局,不求
曲折的情節,注重從看似平凡的小處發掘人物情緒的變化,文筆簡潔而流暢
,注重內心描寫,細膩地傳遞出作者內心渴望生命的抑郁情緒。同時,曼殊
斐爾的作品也是學習英語語法的權威文本,她的小說《園會》、《一杯茶》
等,五十年前就成為英文寫作與英語語法的教學篇目。
《幸福:曼殊斐爾小說集》由民國時期四大纔子之首徐志摩翻譯而成,
他是中國第一位翻譯曼殊斐爾作品的作家,為曼殊斐爾的作品在中國的流布
立下了篳路藍縷之功。譯文後附有完整的英文原文,讀者可以感受英國著名
作家曼殊斐爾的語言魅力。
-
園會
毒藥
巴克媽媽的行狀
一杯茶
幸福
一個理想的家庭
刮風
附錄一 夜深時(殘篇)
附錄二 曼殊斐爾
-
園會
那天的天氣果然是理想的。園會的天氣,就是他們預定的,也沒有再好
的了。沒有風,暖和,天上沒有雲點子。就是藍天裡蓋著一層淡金色的霧紗
,像是初夏有時的天氣。那園丁天亮就起來,剪草,掃地,收拾個干淨;草
地和那種著小菊花的暗暗的平頂的小花房兒,都閃閃地發亮著。還有那些玫
瑰花,她們自個兒真像是懂得,到園會的人們也就隻會得賞識玫瑰花兒;這
是誰都認得的花兒。好幾百,真是好幾百,全在一夜裡開了出來;那一叢綠
綠的全低著頭兒,像是天仙來拜會過他們似的。
他們早餐還沒有喫完,工人們就來安那布篷子。
“娘,你看這篷子安在哪兒好?”
“我的好孩子,用不著問我。今年我是打定主意什麼事都交給你們孩子
們的了。忘了我是你們的娘。隻當我是個請來的貴客就得。”
但是梅格總還不能去監督那些工人們。她沒有喫早飯就洗了頭發,她帶
著一塊青的頭巾坐在那裡喝咖啡,潮的黑的發鬈兒貼在她兩邊的臉上。喬斯
,那蝴蝶兒,每天下來總是穿著綢的裡裙,披著日本的花衫子。
“還是你去吧,勞拉,你是講究美術的。”
勞拉就飛了出去,手裡還拿著她的一塊牛油面包。
她就愛有了推頭到屋子外面喫東西;她又是*愛安排事情的;她總以為
她可以比誰都辦得穩當些。
四個工人,脫了外褂子的,一塊兒站在園裡的道兒上。他們手裡拿著支
篷帳的杆子,一卷卷的帆布,背上掛著裝工具的大口袋兒。他們的神氣很叫
人注意的。勞拉現在倒怪怨她還拿著那片牛油面包,可是又沒有地方放,她
又不能把它擲了。她臉上有點兒紅,她走近他們的時候;可是她裝出嚴厲的
,甚至有點兒近視的樣子。
“早安,”她說,學她娘的口氣。但是這一聲裝得太可怕了,她自己都
有點兒難為情,接著她就像個小女孩子口喫著說,“啊——歐——你們來—
—是不是為那篷帳?”
“就是您哪,小姐,”身子*高的那個說,一個瘦瘦的,滿臉斑點的高
個兒,他掀動著他背上的大口袋,把他的草帽往後腦一推,望下來對著她笑
,“就是為那個。”
他的笑那樣的隨便,那樣的和氣,勞拉也就不覺得難為情了。多麼好的
眼他有的是,小小的,可是那樣的深藍!她現在望著他的同伴,他們也在笑
吟吟的。“放心,我們不咬人的,”他們的笑像在那兒說。工人們多麼好呀
!這早上又是多美呀!可是她不該提起早上,她得辦她的公事。那篷帳。
“我說,把他放在那邊百合花的草地上,怎麼樣呢?那邊成不成?”
她伸著不拿牛油面包的那隻手,點著那百合花的草地。他們轉過身去,
望著她點的方向。那小胖子扁著他那下嘴唇皮兒,那高個子皺著眉頭。
“我瞧不合適,”他說,“看得不夠明亮。您瞧,要是一個漫天帳子,
”他轉身向著勞拉,還是他那隨便的樣子,“您得放著一個地基兒,您一看
就會嘭地一下打著你的眼,要是您懂我的話。”
這一下可是把勞拉蒙住了一陣子,她想不清一個做工的該不該對她說那
樣的話,嘭地一下打著你的眼。她可是很懂得。
“那邊網球場的一個基角兒上呢?”她又出主意。“可是音樂隊也得占
一個基角兒。”
“唔,還有音樂隊不是?”又一個工人說。他的臉是青青的。他的眼睛
瞄著那網球場,神情怪難看的,他在想什麼呢?
“就是一個很小的音樂隊。”勞拉緩緩地說。也許他不會多麼的介意,
要是音樂隊是個小的。但是那高個兒的又打岔了。
“我說,小姐,那個地基兒合適,背著前面那些大樹。那邊兒,準合適
。”
背那些喀拉噶樹。可是那些喀拉噶樹得被遮住了。他們多麼可愛,寬寬
的,發亮的葉子,一球球的黃果子。他們像是你想像長在一個荒島上的大樹
,高傲的,孤單的,對著太陽擎著他們的葉子,果子,冷靜壯麗的神氣。他
們免不了讓那篷帳遮住嗎?
免不了。工人們已經扛起他們的杆子,向著那個地基兒去了。就是那高
個兒的還沒有走。他彎下身子去,捻著一小枝的薰衣草,把他的大拇指與食
指放在鼻子邊,嗅吸了沾著的香氣。勞拉看了他那手勢,把什麼喀拉噶樹全
忘了,她就不懂得一個做工人會注意到那些個東西——愛薰衣草的味兒。她
認識的能有幾個人會做這樣的事。做工人多麼異常的有意思呀,她心裡想。
為什麼她就不能跟做工人做朋友,強如那些粗蠢的男孩子們,伴她跳舞的,
星期日晚上來喫夜飯的?他們準是合適得多。
壞處就在,她心裡打算,一面那高個的工人正在一個信封的後背畫什麼
東西,錯處就在那些個可笑的階級區別,*斃或是絞死了那一點子就沒有事
兒了。就她自個兒說呢,她簡直想不著什麼區別不區別。一點兒,一子兒都
沒有……現在木槌子打樁的聲音已經來了。有人在那兒噓口調子,有人唱了
出來,“你那兒合適不合適,瑪代?”“瑪代!”那要好的意思,那——那
——她想表示她多麼的快活,讓那高個兒的明白她多麼的隨便,她多麼的瞧
不起蠢笨的習慣,勞拉就拿起她手裡的牛油面包來,使勁地啃了一大口,一
面瞪著眼看她的小畫。她覺得她真是個做工的女孩子似的。
“勞拉,勞拉,你在哪兒?有電話,勞拉!”一個聲音從屋子裡叫了出
來。
“來——了!”她就燕子似地掠了去,穿草地,上道兒,上階沿兒,穿
走廊子,進門兒,在前廳裡她的爹與勞裡正在刷他們的帽子,預備辦事去。
“我說,勞拉,”勞裡快快地說,“下半天以前你替我看看我的褂子,
成不成?看看要收拾不要。”“算數。”她說。忽然她自個兒忍不住了。她
跑到勞裡身邊,把他小小地,快快地擠了一下。“啊,我真愛茶會呀,你愛
不愛?”勞拉喘著氣說。
“可——不是,”勞裡用親密的、孩子的口音說,他也拿他的妹妹擠了
一下,把她輕輕地一推,“忙你的電話去,小姐。”
那電話。“對的,對的;對呀。基蒂?早安,我的乖。來喫中飯?一定
來,我的乖。當然好極了。沒有東西,就是頂隨便的便飯——就是面包殼兒
,碎蛋白糖餅殼兒,還有昨天剩下來的什麼。是,這早上天氣真好不是?等
一等——別掛。娘在叫哪。”勞拉坐了下來。
“什麼,娘?聽不著。”
謝裡登太太的聲音從樓梯上飄了下來:“告訴她還是戴她上禮拜天戴的
那頂漂亮帽子。”
“娘說你還是戴你上禮拜天戴的那頂漂亮帽子,好。一點鐘,再會。”
勞拉放回了聽筒,手臂往腦袋背後一甩,深深地呼了一口氣,伸了一個
懶腰,手臂又落了下來。“呼”,她嘆了口氣,快快地重復坐正了。她是靜
靜的,聽著。屋子裡所有的門戶像是全打得大開似的。滿屋子隻是輕的、快
的腳步聲,流動的口音。那扇綠布包著的門,通廚房那一帶去的,不住地擺
著,塞,塞地響。一會兒又聽著一個長長的,氣呼呼的怪響。那是他們在移
動那笨重的鋼琴,圓轉腳兒擦著地板的聲音。但是那空氣!要是你靜著聽,
難道那空氣總是這樣的?小小的,軟弱的風在鬧著玩兒,一會兒往著窗格子
頂上衝了進來,一會兒帶了門兒跑了出去。還有兩小點兒的陽光也在那兒鬧
著玩,一點在墨水瓶上,一點在白銀的照相架上。乖乖的小點子。尤其是在
墨水瓶蓋上的那一點。看的頂親熱的。一個小小的、熱熱的銀星兒。她去親
吻他都成。
前門的小鈴子丁丁地響了,接著薩迪印花布裙子窸窣地上樓梯。一個男
子的口音在含糊地說話,薩迪答話,不使勁地:“我不知道呀。等著。我來
問問謝裡登太太。”
“什麼事,薩迪?”勞拉走進了前廳。
“為那賣花的,勞拉小姐。”
不錯,是的。那邊,靠近門兒,一個寬大的淺盤子,裡面滿放著一盆盆
的粉紅百合花兒。就是一種花。就是百合——美人蕉,大的紅的花朵兒,開
得滿滿的,亮亮的,在鮮艷的、深紅色花梗子上長著,簡直像有靈性的一樣
。
“啊——啊,薩迪!”勞拉說,帶著小小的哭聲似的。她蹲了下去,像
是到百合花的光焰裡去取暖似的;她覺著他們是在她的手指上,在她的口唇
上,在她的心窩裡長著。
“錯了,”她軟音地說。“我們沒有定要這麼多的。薩迪,去問娘去。
”
但是正在這個當兒謝裡登太太也過來了。
“不錯的”,她靜靜地說。“是我定要的。這花兒多麼可愛?”她擠緊
著勞拉的臂膀。“昨天我走過那家花鋪子,我在窗子裡看著了。我想我這一
次總要買他一個痛快。園會不是一個很好的推頭嗎?”
“可是我以為你說過你不來管我們的事。”勞拉說。薩迪已經走開了,
送花來的小工還靠近他的手車站在門外。她伸出手臂去繞著她娘的項頸,輕
輕的,很輕輕的,她咬著他娘的耳朵。
“我的乖孩子,你也不願意有一個過分刻板的娘不是?別孩子氣。挑花
的又來了。”
他又拿進了很多的百合花,滿滿的又是一大盤兒。“一條邊的放著,就
在進門那兒,門框子的兩面,勞駕”,謝裡登太太說。“你看好不好,勞拉
?”
“好,真好,娘。”
在那客廳裡,梅格,喬斯,還有那好的小漢斯,三個人好容易把那鋼琴
移好了。
“我說,把這櫃子靠著牆,屋子裡什麼都搬走,除了椅子,你們看怎麼
樣?”
“成。”
“漢斯,把這幾個桌子搬到休息室裡去,拿一把帚子進來把地毯上的桌
腿子痕子掃了——等一等,漢斯——”喬斯就愛吩咐底下人,他們也愛聽她
。她那神氣就像他們一塊兒在唱戲似的。“要太太、勞拉小姐就上這兒來。
”
“就是,喬斯小姐。”
她又轉身對梅格說話:“我要聽聽那琴**成不成,回頭下半天他們也
許要我唱。我們來試試那‘This life is weary’。”
嘭!他!他,氏!他!那琴聲突然很熱烈地響了出來,喬斯的面色都變
了。她握緊了自己的手。她娘同勞拉剛進來,她對她們望著。一臉的憂郁,
一臉的奧妙。
這樣的生活是疲——倦的,
一滴眼淚,一聲嘆氣。
愛情也是要變——心的
這樣的生活是疲——倦的,
一滴眼淚,一聲嘆氣。
愛情也是不久——長的,
時候到了……再見!
但是她唱到“再見”的時候,雖則琴聲格外地*望了,她的臉上忽然泛
出鮮明的、異常地不同情的笑容。
“我的嗓子成不成,媽媽?”她瞼上亮著。
這樣的生活是疲——倦的,
希望來了,還是要死的。
一場夢景,一場驚醒。
但是現在薩迪打斷了她們。“什麼事,薩迪?”
“說是,太太,廚娘說面包餅上的小紙旗兒有沒有?”
“面包餅上的小紙旗兒,薩迪?”謝裡登太太在夢裡似地回應著。那些
小孩子一看她的臉就知道她沒有小旗兒。
“我想想。”一會兒,她對薩迪堅定地說,“告訴那廚娘等十分鐘我就
給她。”
薩迪去了。
“我說,勞拉”,她母親快快地說,“跟我到休息間裡來。旗子的幾個
名字我寫在一張信封的後背。你來替我寫了出來。梅格,馬上上樓去,把你
頭上那濕東西去了。喬斯,你也馬上去把衣服穿好了。聽著了沒有,孩子們
,要不然回頭你們爹晚上回家的時候我告訴他?說是——喬斯,你要到廚房
裡去,告訴那廚娘別著急,好不好?這早上我怕死了她。”
那張信封好容易在飯間裡那擺鐘背後找了出來。怎麼會在那兒,謝裡登
太太想都想不著了。
“定是你們裡面不知誰從我的手袋裡偷了出來,我記得頂清楚的——奶
酪起司同檸檬奶凍。寫下了沒有?”
“寫了。”
“雞子同——”,謝裡登太太把那張信封擎得遠遠的。“什麼字,看著
像是小老鼠。不會是小老鼠。不是?”
“青果,寶貝。”勞拉說,回過頭來望著。
“可不是,青果,對的。這兩樣東西並著念多怪呀。雞子同青果。”
她們好容易把那幾張旗子寫完。勞拉就拿走到廚房去了。她見喬斯正在
那裡平廚娘的著急,那廚娘可是一點兒也不怕人。
“我從沒有見過這樣精巧的面包餅,”喬斯樂瘋了的口音說。“你說這
兒一共有幾種,廚娘?十五對不對?”
“十五,喬斯小姐。”
“好,廚娘,我恭喜你。”
廚娘手裡拿著切面包餅的長刀,抹下了桌上的碎粉屑兒,開了一張嘴盡
笑。
“戈德伯鋪子裡的來了。”薩迪喊著,從伙食房裡走出來。她看見那人
在窗子外面走過。
這就是說奶油松餅來了。高德伯那家店鋪,就是做奶油松餅出名。有了
他們的,誰都不願意自己在家裡做。
“去拿進來放在桌子上吧,姑娘。”廚娘吩咐。
薩迪去拿了進來,又去了。勞拉與喬斯當然是長大了,不會認真的見了
奶油什麼就上勁。可是她們也就忍不住同聲地贊美,說這松餅做得真可愛呀
。太美了。廚娘動手拾掇,搖下了多餘的糖冰。
“一見這些個松餅兒,像是你一輩子的茶會全回來了似的,你說是不是
?”勞拉說。
“許有的事,”講究實際的喬斯說,她從不想回到從前去的,“他們看
起來這樣美麗輕巧,羽毛似的,我說。”
“一人拿一個吧,我的乖乖,”廚娘說,她那快樂的口音。“你的媽不
會知道的。”
這哪兒成。想想,纔喫早飯,就喫奶油松餅。一想著都叫人難受。可是
要不了兩分鐘,喬斯與勞拉都在舔她們的手指兒了,她們那得意的,心裡快
活的神氣,一看就知道她們是纔喫了新鮮奶油的。
“我們到園裡去,從後門出去,”勞拉出主意。“我要去看看工人們的
篷帳怎麼樣了。那工人們真有意思。”
但是後門的道兒,讓廚娘、薩迪、高德伯鋪子裡的伙計、小漢斯幾個人
攔住了。
出了事了。
“格——格——格”,廚娘咯咯地叫著,像一隻嚇慌了的母雞。薩迪的
一隻手抓緊了她的下巴,像是牙痛似的。小漢斯的臉子像螺旋似的鄒著,摸
不清頭腦。就是高德伯鋪子裡來的伙計看是自己兒得意似的,這故事是他講
的。
“什麼事?出了什麼事?”
“出了大亂子了,”廚娘說,“一個男子死了。”
“一個男子死了!哪兒?怎麼的?什麼時候?”
但是那店伙計可不願意現鮮鮮的新聞,讓人家當著他面搶著講。
“知道那些個小屋子就在這兒下去的,小姐?”知道?當然她知道。“
得,有個年輕的住在那兒,名字叫斯科特,趕大車兒的。他的馬見了那平道
兒的機器,**早上在霍克路的基角兒上,他那馬見了就發傻,一個斛鬥就
把他擲了下去,擲在他腦袋的後背。死了。”
“死了!”勞拉瞪著眼望著那伙計。
“他們把他撿起來的時候就死了,”那伙計講得*起勁了。“我來的時
候正踫著他們把那尸體抬回家去。”他對著廚娘說,“他剩下一個妻子,五
個小的。”
“喬斯,這兒來。”她一把拉住了她妹子的衣袖,牽著她穿過了廚房,
到綠布門的那一面。她停下了,靠在門邊。“喬斯!”她說,嚇壞了的,“
這怎麼辦,我們有什麼法子把什麼事都停了呢?”
“什麼事都停了,勞拉!”喬斯駭然地說。“這怎麼講?”
“把園會停了,當然。”喬斯為什麼要裝假?
但是喬斯反而*糊塗了。“把園會停了?勞拉我的乖,別那麼傻。當然
我們不干這樣的事,也沒有人想我們這麼辦。別太過分了。”
“可是現鮮鮮的有人死在我們的大門外,我們怎麼能舉行園會呢?”
這話實在是太過分了,因為那些小屋子有他們自個兒的一條小巷,在她
們家一直斜下去的那條街的盡頭。中間還隔著一條頂寬的大路哪。不錯,他
們是太貼近一點。那些小屋子看得真讓人眼痛,他們就不應該在這一帶的附
近。就是幾間小小的爛房子,畫成朱古力棕褐色的。他們的背後園裡也就是
菜梗子,瘦小的母雞子,紅茄的罐子。他們煙囪裡冒出來的煙,先就是寒傖
。爛布似的,爛片似的小煙卷兒,哪兒比得上謝裡登家的煙囪裡出來的,那
樣大片的,銀色的羽毛,在天空裡蕩著。洗衣服的婦人們住在那條小巷裡,
還有掃煙囪的,一個補鞋的,還有一個男的,他的門前滿掛著小雀籠子。孩
子們又是成群的。謝裡登家的孩子小的時候,他們是一步也不準上那兒去的
,怕的是他們學下流話,沾染他們下流的脾氣。但是自從他們長成了,勞拉
同勞裡有時也穿著那道兒走。又肮髒,又討厭。他們走過都覺得難受。可是
一個人什麼地方都得去,什麼事情都得親眼看。他們就是這樣地走過了。
“你隻要想想我們的音樂隊一動手,叫那苦惱的婦人怎麼受得住!”勞
拉說。
“啊,勞拉!”喬斯現在認真的著惱了。“要是每次有人踫著了意外,
你的音樂隊就得停起來,你的一輩子也就夠受了。我也是和你一樣的難過。
我也是一樣的軟心腸的。”她的眼睛發狠了。她那盯著她的姊姊的神氣,就
像是她們小時候打架的樣子。“你這樣的感情作用也救不活一個做工的酒鬼
。”她軟軟地說。
“酒鬼!誰說他是酒醉!”勞拉也發狠地對著喬斯。“我馬上就進去告
訴娘去。”她說,正像她從前每次鬧翻了說的話。
“請,我的乖。”喬斯甜著口音說。
“娘呀,我可以到你的房裡嗎?”勞拉手持著那大的玻璃門拳兒。
“來吧,孩子。唉,怎麼回事?怎麼你的臉上紅紅的?”謝裡登太太從
她的鏡臺邊轉了過來。她正在試她的新帽子。
“娘,有一個人摔死了。”勞拉開頭說。
“不是在我們的園裡?”她娘就打岔。
“不,不!”
“啊,你真是嚇了我一跳。”謝裡登太太嘆了口氣,放心了,拿下了她
的大帽子,放在她的膝腿上。
“可是你聽我說,娘,”勞拉說。她把這可怕的故事講了,氣都喘不過
來。“當然,我們不能開茶會了不是,”她懇求地說。“音樂隊,什麼人都
快到了。他們聽得到的,娘;他們差不多是近鄰!”
她娘的態度竟是同喬斯方纔一樣,勞拉真駭然了!*難受的是因為她看
是好玩似的。她竟沒有把勞拉認真對待。
“但是,我的好孩子,你得應用你的常識。這無非是偶然的,我們聽著
了那回事。要是那邊有人生病了——我就不懂得他們擠在那些髒死的小窠兒
裡,怎麼的活法——我們還不是一樣地開我們的茶會不是?”
勞拉隻好回答說“是的”,可是她心裡想這是全錯的。她在她娘的沙發
椅上坐了下來,捻著那椅墊的縐邊。
“娘,這不是我們真的連一點慈悲心都沒有了嗎?”
“乖孩子!”謝裡登太太站起身走過來了,拿著那帽子。勞拉來不及攔
阻,她已經把那帽子套在她的頭上。“我的孩子!”她娘說,“這帽子是你
的。天生是你的。這帽子我戴太嫌年輕了,我從沒有見過你這樣的一張畫似
的。你自己看看。”她就拿著手鏡要她看。
“可是,娘,”勞拉又起了一個頭。她不能看她自己;她把身子轉了過
去。
這一來謝裡登太太可也忍不住了,就像方纔喬斯忍不住了一樣。
“你這是太離奇了,勞拉,”她冷冷地說。“像他們那樣的人家也不想
我們犧牲什麼。況且像你這樣要什麼人都不樂意,也不見怎樣的發善心不是
?”
“我不懂。”勞拉說,她快快地走了出去,進了她自己的臥房。在那裡
,很是無意的,她*先見著的,就是鏡子裡的一個可愛的姑娘,戴著她那黑
帽子金小花兒裝邊的,還有一條長的黑絲絨帶子。她從沒有想過她能有這樣
的好看。娘是對的嗎?她想。現在她竟是希望娘是對的。我不是太過分嗎?
許是太過分了。就是一轉瞬間,她又見著了那可憐的婦人同她的小孩子,她
男人的尸體抬到屋子裡去。但這都是模糊的,不真切的,像新聞紙上的圖畫
似的。等茶會過了我再想著吧,她定主意了。這像是*妥當的辦法了……
中飯喫過一點半。兩點半的時候他們已經準備這場鬧了。穿綠褂子的音
樂隊已經到了,在那網球場的犄角兒上落坐了。
“我的乖!”基蒂·梅特蘭嬌音地說,“可不是他們太像青蝦蟆?你們
應該讓他們圍著那小池子蹲著,讓那領班的站在池中間一張花葉子上。”
勞裡也到了,一路招呼著進去換衣服了。一見著他,勞拉又想起那件禍
事了。她要告訴他。如其勞裡也同其餘的見解一樣,這就不用說一定是不錯
的了。她跟著他進了前廳。
“勞裡!”
“哎!”他已經是半扶梯,但是他轉身來見了勞拉,他就鼓起了他的腮
幫子,睜著大眼睛望著她。“我說,勞拉!你叫我眼都看花了,”勞裡說,
“多,多漂亮的帽子!”
勞拉輕輕地說:“真的嗎?”她仰著頭對勞裡笑著,到底還是沒有告訴
他。
不多一會見客人像潮水一般來了。音樂隊動手了,雇來的聽差忙著從屋
子跑到篷帳裡去。隨你向哪兒望,總有一對對的在緩緩地走著,彎著身子看
花,打招呼,在草地上過去。客人們像是美麗的鳥雀兒,在這下半天停在謝
裡登家的園子裡,順路到——哪兒呢?啊,多快活呀,踫著的全是快活人,
握著手,貼著臉子,對著眼睛笑。
“勞拉乖乖,你多美呀!”
“你的帽子多合適呀,孩子!”
“勞拉,你樣子頂像西班牙美人,我從沒有見你這樣漂亮過。”
勞拉抖擻著,也就軟軟地回答:“你喝了茶沒有?來點兒冰吧;**的
果子冰倒真是別致的。”她跑到她爹那裡去,求著他,“好爹爹,音樂隊讓
他們喝點兒水吧?”
這圓滿的下午漸漸地成熟了,漸漸地衰謝了,漸漸地花瓣兒全閉著了。
“再沒有*滿意的園會……”“大,大成功……”“真要算是*,*…
…”
勞拉幫著她娘說再會。她們一並肩地站在門口,一直等到完事。
“完了,完了,謝謝天,”謝裡登太太說。“把他們全找來,勞拉。我
們去喝一點新鮮咖啡去。我累壞了。總算是很成功的。可是這些茶會,這些
茶會!為什麼你們一定不放過要開茶會!”他們全在走空了的篷帳裡坐了下
來。
“來一塊面包夾餅,爹爹。旗子是我寫的。”
“多謝。”謝裡登先生咬了一口,那塊餅就不見了。他又喫了一塊。“
我想你們沒有聽見**出的駭人的亂子嗎?”
“我的乖,”謝裡登太太說,舉著她的一隻手,“我們聽見的。險一點
把我們的茶會都弄糟了。勞拉硬主張我們把會停了。”
“啊,娘呀!”勞拉不願意為這件事再受嘲諷。
“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不是?”謝裡登先生說。“那死的也成了家了。
就住在這兒下去那個小巷子裡,他拋下了一個妻子,半打小孩,他們說。”
很不自然地小靜了一會。太太的手不安地弄著她的茶杯。實在爹不識趣
了……
忽然她仰起頭來望著。桌子上滿是那些個面包夾餅、蛋糕、奶餅油松,
全沒有喫,回頭全是沒有用的。她想著了她的一個妙主意。
“我知道了,”她說。“我們裝起一個籃子來吧。我們拿點兒這**沒
有動的上好點心,給那可憐的女人吧。隨便怎麼樣,她的小孩子們總有了一
頓大大的食品,你們說對不對?並且她總有鄰舍人等出出進進的。不勞她費
心這全是現成的,可不是個好主意?”
“勞拉!”說著她跳了起來,“把那樓梯邊櫃子裡的那大竹籃子拿來。
”
“但是,娘,你難道真以為這是個好主意嗎?”勞拉說。
又是一次,多奇怪,她的見解與旁人不同了。拿她們茶會餘下的滓子去
給人家。那可憐的婦人真的就會樂意嗎?
“當然啰!**你怎麼的?方纔不多一會兒,你抱怨著人家不發慈悲,
可是現在——”
啊,好的!勞拉跑去把籃子拿來了。裝滿了,堆滿了,她娘自己動手的
。
“你自己拿了去,乖乖,”她說,“你就是這樣去好了。不,等一等,
也帶一點大紅花去。他們那一等人頂喜歡這大花兒的。”
“小心那花梗子毀了她的新花邊衣。”講究實際的喬斯說。
真會的。還好,來得及。“那你就拿這竹籃子吧。喂,勞拉!”她娘跟
她出了篷帳——“隨便怎樣你可不要——”
“什麼,娘?”
不,這種意思還是不裝進孩子的腦袋裡去好!“沒有事!你跑吧!”
勞拉關上園門的時候,天已經快黃昏了。一隻大狗像一個黑影子似的跑
過。這道兒白白的亮著,望下去那塊凹地裡暗沉沉的就是那些小屋子。
過了那半天的熱鬧這時候多靜呀。她現在獨自走下那斜坡去,到一個地
方,那裡說是有個男子死了,她可是有點兒想不清似的。為什麼她想不清?
她停步了一會兒。她的內心像滿蒙著親吻呀,種種的口音呀,杯匙丁當的響
聲呀,笑呀,壓平的青草味呀,塞得滿滿的。她再沒有餘地,放別的東西。
多怪呀!她仰起頭望著蒼白的天,她心裡想著的就是:“對呀,這真是頂滿
意的茶會。”
現在那條大路已經走過了。已經近了那小巷,煙沉沉的、黑沉沉的。披
著圍巾的女人,戴著粗便帽的男人匆忙地走著。有的男人靠在木棚子上;小
孩子們在門前玩著。一陣低低的嗡嗡的聲響,從那卑污的小屋子裡出來。有
的屋子裡有一星的燈亮,一個黑影子,螃蟹似的,在窗子裡移動著。勞拉低
了頭快快地走。她現在倒抱怨沒有裹上一件外衣出來。她的上身衣閃得多亮
呀!還有那黑絲絨飄帶的大帽子——換一頂帽子多好!人家不是望著她嗎?
他們一定在望著她。這一來來錯了;她早知道錯了。她現在再回去怎麼樣呢
?
不,太遲了。這就是那家人家。一定是的,暗暗的一堆人站在外面。門
邊一張椅子裡坐著一個很老的老婆子,手裡拿著一根拐杖,她在看熱鬧,她
的一雙腳踏在一張報紙上。勞拉一走近人聲就停了。這群人也散了。倒像是
他們知道她要到這兒來似的,像是他們在等著她哪。
勞拉異常地不自在。顛著她肩上的絲絨帶子,她問一個站在旁邊的婦人
:“這是斯科特夫人的家嗎?”那個婦人,古怪地笑著,回說:“這是的,
小姑娘。”
啊,這情形躲得了多好!她走上他們門前的走道,伸手敲門的時候,她
真的說了:“幫助我,上帝。”隻要躲得了他們那彈出的眼睛,這是有什麼
法子把自己裹了起來,裹在一個圍肩裡都好。我放下了這籃子就走,她打定
了主意。我連空籃子都不等了。
那門開了。一個穿黑的小女人在暗冥裡替她開著門。
勞拉說:“你是斯科特夫人嗎?”但是那女人的答話嚇了勞拉一跳:“
請進來吧,小姐。”她讓她關進在門裡了。
“不,”勞拉說,“我不進去了。我隻是要放下這籃子。娘叫我送來—
—”
在黑沉沉的夾道兒裡的小女人像是沒有聽著似的。“走這兒,請,小姐
。”她軟媚的口音說,勞拉跟了進去。
她進了一間破爛的,又低又窄的廚房,臺上一盞冒煙的油燈。灶火的前
面有一個婦人坐著。
“艾姆,”引她進去的那個小個兒說。“艾姆,是個小姑娘。”她轉身
對著勞拉。她有意味地說:“我是她的妹子,小姐。您得原諒她不是?”
“啊,可是當然。”勞拉說。“請,請不要打攪她。我——我隻要放下
——”
但是這時候坐在灶火前的婦人轉了過來。她的臉子,腫脹著,紅紅的,
紅腫的眼,紅腫的口唇,看得可怕。她看是摸不清為什麼勞拉在那兒。這算
什麼意思?為什麼一個外客拿著一個籃子站在她的廚房裡?這是什麼回事?
她那可憐的臉子又是緊緊地皺了起來。
“我有數,”還是那個人說。“我會謝小姑娘的。”
她又說了:“您得原諒她,小姐,我想你一定。”她的臉子,也是腫腫
的,想來一個討好的笑容。
勞拉隻求馬上出去,馬上走開。她已經回上了那條通道。那門開了。她
一直走過去,走進那間臥房,那死人就攤在那裡。
“您得看看他不是?”艾姆的妹子說,她匆匆跑上前去到那床邊,“不
要怕,我的姑娘,”——現在她的口音變得很愛惜,很機敏似的,她愛憐地
把死人身上的被單拉下了——“他像一幅畫。什麼怪相也沒有。過來,我的
乖。”
勞拉過來了。
一個年輕的人躺在那裡,深深地睡著——睡得這樣的沉,這樣的深,他
看是離他們倆遠著哪。啊,這樣隔著遠遠的,這樣的平靜。他在做夢,從此
不要驚醒他了。他的頭深深地落在枕頭上,他的眼緊閉著,眼睛在緊閉了的
眼睛子裡是盲的了。他全交給他的夢了。什麼園會呀,竹籃子呀,花邊衣呀
,與他有什麼相干。他離開那些個事情遠著哪。他是神奇的,美麗的了。一
面他們在那裡歡笑,一面音樂隊在那裡奏樂,這件不可思議的事到了這條小
巷裡。快活……快活……什麼都好了,睡著的臉子在說。這正是該的。我是
滿足了。
但是我總得哭一哭,她要出這屋子總得對他說幾句話。勞拉響響地孩子
似的哭了一聲。
“饒恕我的帽子。”她說。
這時候她也不等艾姆的妹子了。她自己走出了門,下了走道,經過那些
黑沉沉的人們。在那巷子的轉角上她踫著了勞裡。
他從黑蔭裡走了出來。“是你嗎,勞拉?”
“是我。”
“娘著急了,沒有什麼嗎?”
“是,很好。啊,勞裡!”她挽住他的臂膀,緊緊地靠著他。
“我說,你沒有哭不是?”她的兄弟問。
勞拉搖著她的頭。她是哭著哩。
勞裡拿手圍著她的肩膀。“不要哭,”他那親熱的,愛憐的口音說,“
那邊難受不是?”
“不,”勞拉悲哽地說。“這太不可思議了,但是,勞裡——”她停頓
了,她望著她的兄弟。“生命是不是,”她打頓地說,“生命是不是——”
但是生命是什麼她說不上。不礙。他很懂得。
“可不是,乖乖?”勞裡說。
P1-26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