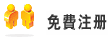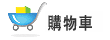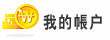| | | | 呼蘭河傳 | | 該商品所屬分類:小說 -> 中國古典小說 | | 【市場價】 | 219-318元 | | 【優惠價】 | 137-199元 | | 【介質】 | book | | 【ISBN】 | 9787569919110 | | 【折扣說明】 | 一次購物滿999元台幣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2000元台幣95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3000元台幣92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4000元台幣88折+免運費+贈品
| | 【本期贈品】 | ①優質無紡布環保袋,做工棒!②品牌簽字筆 ③品牌手帕紙巾
|
|
| 版本 | 正版全新電子版PDF檔 | | 您已选择: | 正版全新 | 溫馨提示:如果有多種選項,請先選擇再點擊加入購物車。*. 電子圖書價格是0.69折,例如了得網價格是100元,電子書pdf的價格則是69元。
*. 購買電子書不支持貨到付款,購買時選擇atm或者超商、PayPal付款。付款後1-24小時內通過郵件傳輸給您。
*. 如果收到的電子書不滿意,可以聯絡我們退款。謝謝。 | | | |
| | 內容介紹 | |

-
出版社: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
ISBN:9787569919110
-
作者:蕭紅
-
頁數:302
-
出版日期:2018-01-01
-
包裝:平裝
-
開本:32開
-
字數:190千字
-
? 教育部新課標**書目。
? 原汁原味——忠實復原1941年由桂林河山出版社**出版版本。
? 影響數代人的經典——中國現代詩性小說扛鼎之作,20世紀中文小說百強第九位,30年代文學洛神、四大纔女之一蕭紅**時代的文學經典。
? 備受魯迅、茅盾、夏志清等名家贊譽——以女性的目光洞悉歷史的真實,達到對現代文明以及國民靈魂的徹悟。
? 蕭紅短暫人生生涯的一部“回憶式”長篇小說——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座蕭紅筆下的“後花園”,那裡有故鄉、親人、往事,有讓一個人走下去的勇氣和力量。
? 封面采用原版元素,致敬經典!
-
《呼蘭河傳》是蕭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這部作品被香港“亞洲文壇”評為20世紀中文小說百強第九位。在《呼蘭河傳》這部作品中,作者以散文化的筆調描寫了以家鄉為原型的“呼蘭河城”的傳記。全書共分,七章,它以作者的童年回憶為引線,描繪了20世紀20年代東北小城呼蘭的種種人和事,真實而生動地再現了當地老百姓平凡、卑瑣、落後的生活現狀和得過且過、平庸、愚昧的精神狀態。但蕭紅還是用淡泊的語氣和包容的心敘說了家鄉的種種。她將一片片記憶的碎片擺出來,回味那份獨屬於童年、獨屬於鄉土的氣息。
-
蕭紅(1911-1942),中國近現代女作家,“民國四大纔女”之一,被譽為“20世紀30年代的文學洛神”。1911年,出生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呼蘭區一個封建地主家庭,幼年喪母。1932年,結識蕭軍。1933年,以悄吟為筆名發表第一篇小說《棄兒》。1935年,在魯迅的支持下,發表成名作《生死場》。1936年,東渡日本,創作散文《孤獨的生活》、長篇組詩《砂粒》等。1940年,與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後發表中篇小說《馬伯樂》、長篇小說《呼蘭河傳》等。1942年1月22日,因肺結核和惡性氣管擴張病逝於香港,年僅31歲。
-
目錄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51
第三章 / 085
第四章 / 129
第五章 / 157
第六章 / 219
第七章 / 259
尾聲 / 299
-
嚴鼕一封鎖了大地的時候,則大地滿地裂著口。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幾尺長的,一丈長的,還有好幾丈長的,它們毫無方向地,便隨時隨地,隻要嚴鼕一到,大地就裂開口了。
嚴寒把大地凍裂了。
年老的人,一進屋用掃帚掃著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說:
“**好冷啊!地凍裂了。”
趕車的車夫,頂著三星,繞著大鞭子走了六七十裡,天剛一蒙亮,進了大店,**句話就向客棧掌櫃的說:
“好厲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樣。”
等進了棧房,摘下狗皮帽子來,抽一袋煙之後,伸手去拿熱饅頭的時候,那伸出來的手在手背上有無數的裂口。
人的手被凍裂了。
賣豆腐的人清早起來,沿著人家去叫賣,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盤貼在地上拿不起來了。被凍在地上了。
賣饅頭的老頭,背著木箱子,裡邊裝著熱饅頭,太陽一出來,就在街上叫喚。他剛一從家裡出來的時候,他走的快,他喊的聲音也大。可是過不了一會,他的腳上掛了掌子了,在腳心上好像踏著一個雞蛋似的,圓滾滾的。原來冰雪封滿了他的腳底了。使他走起來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加著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這樣,也還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饅頭箱子跌翻了,饅頭從箱底一個一個的跑了出來。旁邊若有人看見,趁著這機會,趁著老頭子倒下一時還爬不起來的時候,就拾了幾個一邊喫著就走了。等老頭子掙扎起來,連饅頭帶冰雪一起檢蕭紅的文章中,有部分字詞反映了當時或自己的用字習慣,與現在常用字不同。本書保留這部分異形字詞的原有寫法,盡量恢復初刊原貌。到箱子去,一數,不對數。他明白了。他向著那走不太遠的喫他饅頭的人說:
“好冷的天,地皮凍裂了,吞了我的饅頭了。”
行路人聽了這話都笑了。他背起箱子來再往前走,那腳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結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難,於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掛越多,而且因為呼吸的關繫,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掛了霜了。這老頭越走越慢,擔心受怕,顫顫驚驚,好像初次穿上了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場似的。
小狗凍得夜夜的叫喚,哽哽的,好像它的腳爪被火燒著了一樣。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凍裂了;
井被凍住了;
大風雪的夜裡,竟會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來,一推門,竟推不開門了。
大地一到了這嚴寒的季節,一切都變了樣,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風之後,呈著一種混沌沌的氣像,而且整天飛著清雪。人們走起路來是快的,嘴裡邊的呼吸,一遇到了嚴寒好像冒著煙似的。七匹馬拉著一輛大車,在曠野上成串的一輛挨著一輛的跑,打著燈籠,甩著大鞭子,天空掛著三星。跑了二裡路之後,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這一批人馬在冰天雪地裡邊竟熱氣騰騰的了。一直到太陽出來,進了棧房,那些馬纔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馬毛立刻就上了霜。
人和馬喫飽了之後,他們再跑。這寒帶的地方,人家很少,不像南方,走了一村,不遠又來了一村,過了一鎮,不遠又來了一鎮。這裡是什麼也看不見,遠望出去是一片白。從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見的。隻有憑了認路的人的記憶纔知道是走向了什麼方向。拉著糧食的七匹馬的大車,是到他們附近的城裡去。載來大豆的賣了大豆,載來高粱的賣了高粱。等回去的時候,他們帶了油、鹽和布匹。
呼蘭河就是這樣的小城,這小城並不怎樣繁華,隻有兩條大街,一條從南到北,一條從東到西,而*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華。十字街上有金銀首飾店,布莊,油鹽店,茶莊,藥店,也有撥牙的洋醫生。那醫生的門前,掛著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畫著特別大的有量米的鬥那麼大的一排牙齒。這廣告在這小城裡邊無乃太不相當,使人們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因為油店,布店和鹽店,他們都沒有什麼廣告,也不過是鹽店門前寫個“鹽”字,布店門前掛了兩張怕是自古亦有之的兩張布幌子。其餘的如藥店的招牌,也不過是把那戴著花鏡的伸出手去在小枕頭上號著婦女們的脈管的醫生的名字掛在門外就是了。比方那醫生的名字叫李永春,那藥店也就叫“李永春”。人們憑著記憶,哪怕就是李永春摘掉了他的招牌,人們也都知李永春是在那裡。不但城裡的人這樣,就是從鄉下來的人也多少都把這城裡的街道,和街道上盡是些什麼都記熟了。用不著什麼廣告,用不著什麼招引的方式,要買的比如油鹽、布匹之類,自己走進去就會買。不需要的,你就是掛了多大的牌子,人們也是不去買。那牙醫生就是一個例子,那從鄉下來的人們看了這麼大的牙齒,真是覺得希奇古怪,所以那**子前邊,停了許多人在看,看也看不出是什麼道理來。假若他是正在牙痛,他也**的不去讓那用洋法子的醫生給他撥掉,也還是走到李永春藥店去,買二兩黃連,回家去含著算了吧!因為那牌子上的牙齒太大了,有點莫名其妙,怪害怕的。
所以那牙醫生,掛了兩三年招牌,到那裡去撥牙的卻是寥寥無幾。
後來那女醫生沒有辦法,大概是生活沒法維持,她兼做了收生婆。
城裡除了十字街之外,還有兩條街,一個叫做東二道街,一個叫做西二道街。這兩條街是從南到北的,大概五六裡長。這兩條街上沒有什麼好記載的,有幾座廟,有幾家燒餅鋪,有幾家糧棧。
東二道街上有一家火磨火磨:用電動機或內燃機帶動的磨。此處代指面粉加工廠。,那火磨的院子很大,用紅色的好磚砌起來的大煙筒是**高的,聽說那火磨裡邊進去不得,那裡邊的消信可多了,是踫不得的。一踫就會把人用火燒死,不然為什麼叫火磨呢?就是因為有火,聽說那裡邊不用馬,或是毛驢拉磨,用的是火。一般人以為盡是用火,豈不把火磨燒著了嗎?想來想去,想不明白,越想也就越糊塗。偏偏那火磨又是不準參觀的。聽說門口站著守衛。
東二道街上還有兩家學堂,一個在南頭,一個在北頭。都是在廟裡邊,一個在龍王廟裡,一個在祖師廟裡。兩個都是小學。
龍王廟裡的那個學的是養蠶,叫做農業學校。祖師廟裡的那個,是個普通的小學,還有**班,所以又叫做高等小學。
這兩個學校,名目上雖然不同,實際上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也不過那叫做農業學校的,到了秋天把蠶用油炒起來,教員們大喫幾頓就是了。
那叫做高等小學的,沒有蠶喫,那裡邊的學生的確比農業學校的學生長的高,農業學生開頭是念“人、手、足、刀、尺”,頂大的也不過十六七歲。那高等小學的學生卻不同了,吹著洋號,竟有二十四歲的,在鄉下私學館裡已經教了四五年的書了,現在纔來上高等小學。也有在糧棧裡當了二年的管賬先生的現在也來上學了。
這小學的學生寫起家信來,竟有寫到:“小禿子鬧眼睛好了沒有?”小禿子就是他的八歲的長公子的小名。次公子,女公子還都沒有寫上,若都寫上怕是把信寫得太長了。因為他已經子女成群,已經是一家之主了,寫起信來總是多談一些個家政,姓王的地戶的地租送來沒有?大豆賣了沒有?行情如何之類。
這樣的學生,在課堂裡邊也是極有地位的,教師也得尊敬他,一不留心,他這樣的學生就站起來了,手裡拿著《康熙字典》,常常會把先生指問住的。萬裡干坤的“亁”和干菜干菜:蔬菜的干制品。的“干”,據這學生說是不同的,干菜的“干”應該這樣寫:“亁”,而不是那樣寫:“干”。
西二道街上不但沒有火磨,學堂也就隻有一個。是個清真學校,設在城隍廟裡邊。
其餘的也和東二道街一樣,灰禿禿的,若有車馬走過,則煙塵滾滾,下了雨滿地是泥。而且東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個,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漿好像粥一樣,下了雨,這泥坑就便成河了,附近的人家,就要喫它的苦頭,衝了人家裡滿滿是泥,等坑水一落了去,天一晴了,被太陽一曬出來很多蚊子飛到附近的人家去。同時那泥坑也就越曬越純淨,好像在提煉什麼似的,好像要從那泥坑裡邊提煉出點什麼來似的。若是一個月以上不下雨,那大泥坑的質度*純了,水份**被蒸發走了,那裡邊的泥,又黏又黑,比粥鍋瀲糊,比漿糊還粘。好像煉膠的大鍋似的,黑糊糊的,油亮亮的,那怕蒼蠅蚊子從那裡一飛也要粘住的。
小燕子是很喜歡水的,有時誤飛到這泥坑上來,用翅子點著水,看起來很危險,差一點沒有被泥坑陷害了它,差一點沒有被粘住,趕快頭也不回地飛跑了。
若是一匹馬,那就不然了,非粘住不可。而不僅僅是粘住,而且把它陷進去,馬在那裡邊滾著,掙扎著,掙扎了一會,沒有了力氣那馬就躺下了,一躺下那就很危險,很有致命的可能。但是這種時候不很多,很少有人牽著馬或是拉著車子來冒這種險。
這大泥坑出亂子的時候,多半是在旱年,若兩三個月不下雨這泥坑子纔到了真正危險的時候。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越下雨越壞,一下了雨好像小河似的了,該多麼危險,有一丈來深,人掉下去也要沒頂的。其實不然,呼蘭河這城裡的人沒有這麼傻,他們都曉得這個坑是很厲害的,沒有一個人敢有這樣大的膽子牽著馬從這泥坑上過。
可是若三個月不下雨,這泥坑子就****的干下去,到後來也不過是二三尺深,有些勇敢者就試探著冒險地趕著車從上邊過去了,還有些次勇敢者,看著別人過去,也就跟著過去了,一來二去的,這坑子的兩岸,就壓成車輪經過的車轍了。那再後來者,一看,前邊已經有人走在先了,這懦怯者比之勇敢的人*勇敢,趕著車子走上去了。
誰知這泥坑子的底是高低不平的,人家過去了,可是他卻翻了車了。
車夫從泥坑爬出來,弄得和個小鬼似的,滿臉泥污,而後再從泥中往外挖掘他的馬,不料那馬已經倒在泥污之中了,這時候有些過路的人,也就走上前來,幫忙施救。
這過路的人分成兩種,一種是穿著長袍短褂的,**清潔。看那樣子也伸不出手來,因為他的手也是很潔淨的。不用說那就是紳士**的人物了,他們是站在一旁參觀的。
看那馬要站起來了,他們就喝彩,“噢!噢!”地喊叫著,看那馬又站不起來,又倒下去了,這時他們又是喝彩,“噢噢”的又叫了幾聲。不過這喝的是倒彩。
就這樣的馬要站起來,而又站不起來的鬧了一陣之後,仍是沒有站起來,仍是照原樣可憐地躺在那裡。這時候,那些看熱鬧的覺得也不過如此,也沒有什麼新花樣了。於是星散開去,各自回家去了。
現在再來說那馬還是在那裡躺著,那些幫忙救馬的過路人,都是些普通的老百姓,是這城裡的擔蔥的,賣菜的,瓦匠,車夫之流。他們卷卷褲腳,脫了鞋子,看看沒有什麼辦法,走下泥坑去,想用幾個人的力量把那馬抬起來。
結果抬不起來了,那馬的呼吸不大多了。於是人們著了慌,趕快解了馬套。從車子上把馬解下來,以為這回那馬毫無擔負的就可以站起來了。
不料那馬還是站不起來。馬的腦袋露在泥漿的外邊,兩個耳朵哆嗦著,眼睛閉著,鼻子往外噴著禿禿的氣。
看了這樣可憐的景像,附近的人們跑回家去,取了繩索,拿了絞錐。用繩子把馬捆了起來,用絞錐從下邊掘著。人們喊著號令,好像造房子或是架橋梁似的,把馬抬出來了。
馬是沒有死,躺在道旁。人們給馬澆了一些水,還給馬洗了一個臉。
看熱鬧的也有來的,也有去的。
第二天大家都說:
“那大水泡子又淹死了一匹馬。”
雖然馬沒有死,一哄起來就說馬死了。若不這樣說,覺得那大泥坑也太沒有什麼威嚴了。
在這大泥坑上翻車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一年除了被鼕天凍住的季節之外,其餘的時間,這大泥坑子像它被賦給生命了似的,它是活的。水漲了,水落了,過些日子大了,過些日子又小了。大家對它都起著無限的關切。
水大的時候,不但阻礙了車馬,且也阻礙了行人。老頭走在泥坑子的沿上,兩條腿打顫,小孩子在泥坑子的沿上嚇得狼哭鬼叫。
一下起雨來這大泥坑子白亮亮的漲得溜溜的滿,漲到兩邊的人家的牆根上去了,把人家的牆根給淹沒了。來往過路的人,一走到這裡,就像在人生的路上踫到了打擊。是要奮鬥的,卷起袖子來,咬緊了牙根,全身的精力集中起來,手抓著人家的板牆,心髒撲通撲通的跳,頭不要暈,眼睛不要花,要沉著迎戰。
偏偏那人家的板牆造得又**的平滑整齊,好像有意在危難的時候不幫人家的忙似的,使那行路人不管怎樣巧妙的伸出手來,也得不到那板牆的憐憫,東抓抓不著什麼,西摸也摸不到什麼,平滑得連一個疤拉節子也沒有,這可不知道是什麼山上長的木頭,長得這樣完好無缺。
掙扎了五六分鐘之後,總算是過去了。弄得滿頭流汗,滿身發燒,那都不說。再說那後來的人,依法*制,那花樣也不多,也隻是東抓抓,西摸摸。弄了五六分鐘之後,又過去了。
一過去了可就精神飽滿,哈哈大笑著,回頭向那後來的人,向那正在艱苦階段上奮鬥著的人說:
“這算什麼,一輩子不走幾回險路那不算英雄。”
可也不然,也不一定都是精神飽滿的,而大半是被嚇得臉色發白。有的雖然已經過去了,還是不能夠很快的抬起腿來走路,因為那腿還在打顫。
這一類膽小的人,雖然是險路已經過去了,但是心裡邊無由的生起來一種感傷的情緒,心裡顫抖抖的,好像被這大泥坑子所感動了似的,總要回過頭來望了一望,打量一會,似乎要有些話說。終於也沒有說什麼,還是走了。
有**,下大雨的時候,一個小孩子掉下去,讓一個賣豆腐的救了上來。
救上來一看,那孩子是農業學校校長的兒子。
於是議論紛紛了,有的說是因為農業學堂設在廟裡邊,衝了龍王爺了,龍王爺要降大雨淹死這孩子。
有的說不然,**不是這樣,都是因為這孩子的父親的關繫,他父親在講堂上指手畫腳的講,講給學生們說,說這天下雨不是在天的龍王爺下的雨,他說沒有龍王爺。你看這不把龍王爺活活的氣死,他這口氣那能不出呢?所以就抓住了他的兒子來實行因果報應了。
有的說,那學堂裡的學生也太不像樣了,有的爬上了老龍王的頭頂,給老龍王去戴了一個草帽。這是什麼年頭,一個毛孩子就敢惹這麼大的禍,老龍王怎麼會不報應呢?看著吧,這還不能算了事,你想龍王爺並不是白人白人:平民百姓。呵!你若惹了他,他可能夠饒了你?那不像對付一個拉車的,賣菜的,隨便的踢他們一腳就讓他們去。那是龍王爺呀!龍王爺還是惹得的嗎?
有的說,那學堂的學生都太不像樣了,他說他親眼看見過,學生們拿了蠶放在大殿上老龍王的手上。你想老龍王那能夠受得了。
有的說,現在的學堂太不好了,有孩子是千萬上不得學堂的。一上了學堂就天地人鬼神不分了。
有的說他要到學堂把他的兒子領回來,不讓他念書了。
有的說孩子在學堂裡念書,是越念越壞,比方嚇掉了魂,他娘給他叫魂的時候,你聽他說什麼?他說這叫迷信。你說再念下去那還了得嗎?
說來說去,越說越遠了。
過了幾天,大泥坑子又落下去了,泥坑兩岸的行人通行無阻。
再過些日子不下雨,泥坑子就又有點像要干了。這時候,又有車馬開始在上面走,又有車子翻在上面,又有馬倒在泥中打滾,又是繩索棍棒之類的,往外抬馬,被抬出去的趕著車子走了。後來的,陷進去,再抬。
一年之中抬車抬馬,在這泥坑子上不知抬了多少次,可沒有一個人說把泥坑子用土填起來不就好了嗎?沒有一個。
有一次一個老紳士在泥坑漲水時掉在裡邊了。一爬出來,他就說:
“這街道太窄了,去了這水泡子連走路的地方都沒有了。這兩邊的院子,怎麼不把院牆拆了讓出一塊來?”
他正說著,板牆裡邊,就是那院中的老太太搭了言。她說院牆是拆不得的,她說*好種樹,若是沿著牆根種上一排樹,下起雨來人就可以攀著樹過去了。
說拆牆的有,說種樹的有,若說用土把泥坑來填平的,一個人也沒有。
這泥坑子裡邊淹死過小豬,用泥漿悶死過狗,悶死過貓,雞和鴨也常常死在這泥坑裡邊。
原因是這泥坑上邊結了一層硬殼,動物們不認識那硬殼下面就是陷阱,等曉得了可也就晚了。它們跑著或是飛著,等往那硬殼上一落可就再也站不起來了。白天還好,或者有人又要來施救。夜晚可就沒有辦法了。它們自己掙扎,掙扎到沒有力量的時候就很自然的沉下去了,其實也或者越掙扎越沉下去的快。有時至死也還不沉下去的事也有。若是那泥漿的密度過高的時候,就有這樣的事。
比方肉上市。忽然賣便宜豬肉了,於是大家就想起那泥坑子來了,說:
“可不是那泥坑子裡邊又淹死了豬了?”
說著若是腿快的,就趕快跑到鄰人的家去,告訴鄰居:
“快去買便宜肉吧,快去吧,快去吧,一會沒有了。”
等買回家來纔細看一番,似乎有點不大對,怎麼這肉又紫又青的!可不要是瘟豬肉。
但是又一想,那能是瘟豬肉呢,一定是那泥坑子淹死的。
於是煎,炒,蒸,煮,家家喫起便宜豬肉來。雖然喫起來了,但就總覺得不大香,怕還是瘟豬肉。
可是又一想,瘟豬肉怎麼可以喫得,那麼還是泥坑子淹死的吧!
本來這泥坑子一年隻淹死一兩口豬,或兩三口豬,有幾年還連一個豬也沒有淹死。至於居民們常喫淹死的豬肉,這可不知是怎麼一回事,真是龍王爺曉得。
雖然喫的自己說是泥坑子淹死的豬肉,但也有喫病了的,那喫病了的就大發議論說:
“就是淹死的豬肉也不應該抬到市上去賣,死豬肉終究是不新鮮的,稅局子是干什麼的,讓大街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賣起死豬肉來?”
那也是喫了死豬肉的,但是尚且沒有病的人說:
“話可也不能是那麼說,一定是你疑心,你三心二意的喫下去還會好。你看我們也一樣的喫了,可怎麼沒病?”
間或也有小孩子太不知時務,他說他媽不讓他喫,說那是瘟豬肉。
這樣的孩子,大家都不喜歡。大家都用眼睛瞪著他,說他:
“瞎說,瞎說!”
有一次一個孩子說那豬肉一定是瘟豬肉,並且是當著母親的面向鄰人說的。
那鄰人聽了倒並沒有堅決的表示什麼,可是他的母親的臉立刻就紅了。伸出手去就打了那孩子。
那孩子很固執,仍是說:
“是瘟豬肉嗎!是瘟豬肉嗎!”
母親實在難為情起來,就拾起門旁的燒火的叉子,向著那孩子的肩膀就打了過去。
於是孩子一邊哭著一邊跑回家裡去了。
一進門,炕沿上坐著外祖母,那孩子一邊哭著一邊撲到外祖母的懷裡說:
“姥姥,你喫的不是瘟豬肉嗎?我媽打我。”
外祖母對這打得可憐的孩子本想安慰一番,但是一抬頭看見了同院的老李家的奶媽站在門口往裡看。
於是外祖母就掀起孩子後衣襟來,用力的在孩子的屁股上啌啌的打起來,嘴裡還說著:
“誰讓你這麼一點你就胡說八道!”
一直打到李家的奶媽抱著孩子走了纔算完事。
那孩子哭得一塌糊塗,什麼“瘟豬肉”不“瘟豬肉”的,哭得也說不清了。
總共這泥坑子施給當地居民的福利有兩條:
**條:常常抬車抬馬,淹雞,淹鴨,鬧得**熱鬧,可使居民說長道短,得以消遣。
第二條就是這豬肉的問題了,若沒有這泥坑子,可怎麼喫瘟豬肉呢?喫是可以喫的,但是可怎麼說法呢?真正說是喫的瘟豬肉,豈不太不講衛生了嗎?有這泥坑子可就好辦,可以使瘟豬變成淹豬,居民們買起肉來,**經濟,第二也不算什麼不衛生。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