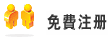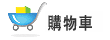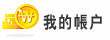| | | | 荷爾德林詩集 | | 該商品所屬分類:文學 -> 外國詩歌 | | 【市場價】 | 473-686元 | | 【優惠價】 | 296-429元 | | 【介質】 | book | | 【ISBN】 | 9787020110841 | | 【折扣說明】 | 一次購物滿999元台幣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2000元台幣95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3000元台幣92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4000元台幣88折+免運費+贈品
| | 【本期贈品】 | ①優質無紡布環保袋,做工棒!②品牌簽字筆 ③品牌手帕紙巾
|
|
| 版本 | 正版全新電子版PDF檔 | | 您已选择: | 正版全新 | 溫馨提示:如果有多種選項,請先選擇再點擊加入購物車。*. 電子圖書價格是0.69折,例如了得網價格是100元,電子書pdf的價格則是69元。
*. 購買電子書不支持貨到付款,購買時選擇atm或者超商、PayPal付款。付款後1-24小時內通過郵件傳輸給您。
*. 如果收到的電子書不滿意,可以聯絡我們退款。謝謝。 | | | |
| | 內容介紹 | |

-
出版社:人民文學
-
ISBN:9787020110841
-
作者:(德)荷爾德林|譯者:王佐良
-
頁數:528
-
出版日期:2016-01-01
-
印刷日期:2016-01-01
-
包裝:平裝
-
開本:16開
-
版次:1
-
印次:1
-
字數:400千字
-
本書收錄了荷爾德林的*大部分詩歌,共計一百六十七首,包含了詩人所創作的頌詩、頌歌、悲歌、短詩和箴言詩。以**的德語版精編《荷爾德林詩全集》為底本譯出,原編者給出的必要注釋和說明文字亦一並譯出。 作者在各個時期的代表作都囊括其中,如《內卡河》《生命的歷程》《橡樹林》《致以太》,以及眾多長詩如《還鄉》《日耳曼尼亞》《萊茵河》《帕特摩斯》《恩培多克勒》《懷念》等,尤其是他的長篇頌歌《和平慶典》,無一遺漏。其中,詩人的代表作《狄奧提瑪》收錄了九個稿本的寫作內容,《人民之聲》兩個稿本,《帕特摩斯》兩個稿本,《**者》兩個稿本。對比和研究荷爾德林的改寫,是很有興味的閱讀形式。這種編排體例,或能有助於讀者深入觀察荷爾德林的詩藝和內心。
-
弗裡德裡希·荷爾德林(1770—1843),德國詩人
。十四歲開始寫詩,年過三十便精神失常。他的詩歌
大量使用精巧、自由的表達,大膽的隱喻,以及對傳
統準則的突破,使他成為德國現代詩歌的先驅。荷爾
德林生前默默無聞,死後作品纔逐漸為人所知,尤其
是進入二十世紀後,尼采和海德格爾等哲學家和詩人
對他的評價越來越高,視其為精神導師。
《荷爾德林詩集》以德國古典出版社2005年出版
的注釋本《荷爾德林詩全集》為底本,收錄了荷爾德
林的絕大部分詩歌,共計一百七十七首,包含了詩人
所創作的頌詩、悲歌、短詩和箴言詩等各種體裁的詩
歌,是國內迄令為止最完整的《荷爾德林詩集》。
詩人的勇氣
難道芸芸眾生皆非你的親戚,
命運女神也不曾親自哺育你?
放心地去浪跡吧,
你的人生,無所憂慮!
你經歷之一切,皆為賜福於你,
皆為你之歡娛!如有什麼讓你
受辱,心靈!無論有
何遭際,你何去何從?
自從歌聲平和地掙脫僵死的
雙唇,在苦難和幸運中皆虔誠,
人類之哲人心靈
愉悅,我們也曾如此,
我們,大眾的歌手,願置身生者,
那裡眾生雲集,歡娛,人皆可愛,
皆坦誠;我們祖先,
那太陽神,亦是如此,
他賜予窮人和富人快樂時日,
在飛逝之光陰,把我們,瞬息的
生靈,如牽引孩童,
扶正2於金色的護帶。
那朱紫的潮水,在等待他,抓持
他,那裡時光到來;看!高貴之光,
諳熟自然之變遷,
沉著鎮定走下小徑。
就這樣去吧,因時間一向如此,
精神從不缺少其權利,歡樂曾
在生命的嚴肅中
死去,卻是美麗的死!
-
荷爾德林(1770—1843),德國詩人。十四歲開始寫詩,剛過三十歲就得了癲狂癥。他的詩歌運用大量隱喻、像征、悖論等現代技巧,突破古典時代的規則束縛,表達對自由的強烈向往和對詩意棲居的生命境界持之以恆的想像。荷爾德林生前默默無聞,死後他的作品進纔逐漸為人們傳誦,尤其是進入二十世紀後,哲學家和詩人對他的評價越來越高,把他看作先驅和導師。
-
1788—1793
男人的歡呼
史書
致**
神聖的軌道
開普勒
在梯爾的墓前
古斯塔夫·阿道夫
為古斯塔夫·阿道夫寫的組詩的結尾
施瓦本少女
憤怒的追求
致安寧
致名譽
曾經和現在
哀悼者的智慧
蒂賓根堡
友誼之歌
愛之歌
致寧靜
不朽頌
我的痊愈
旋律
希臘守護神頌
致麗達
和諧女神頌
繆斯頌
自由頌
瑞士州
人性頌
美人頌
自由頌
友誼頌
愛情頌
青春守護神頌
致一朵玫瑰
致希勒
給諾伊菲爾的邀請
致勇氣的守護神
希臘
1794—1795
致諾伊菲爾
命運
友誼的願望
致青春之神
致大自然
1796-1798
……
1798-1800
1800-1805
1806-1843(後期的詩)
附錄 在可愛的藍天下
譯後記
-
荷爾德林的詩
(代序)
[德]約亨·施密特
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卷荷爾德林的詩集面世。*早在1826年,當他陷入精神黑暗的二十年之後,一本由路德維希·烏蘭德和古斯塔夫·施瓦布合編的小詩集纔得以出版,其中收集的詩還不到所有流傳下來的抒情詩的一半,可是它引發了對荷爾德林已發表作品的**次搜集。荷爾德林生前發表的作品散見於《繆斯年鋻》和其他的文學期刊,其餘的隱藏於極難辨認的手稿中。直到二十世紀的1954年,他*重要的一首贊美詩《和平慶典》纔被人們發現。
十九世紀這位詩人充其量隻有抒情小說《許佩裡翁》(Hyperion)讓他有點名氣,人們很少了解、也很少關注他的詩,即使是那些屬於德國文學中***的作品,例如《生命的半程》,那時候的人們也未能理解。但二十世紀伊始,情況發生了變化。一種新的、由現代抒情詩激發起來的、對抒情詩人荷爾德林的關注迅速達到了高潮。特別是他1800年以後的詩作,那毫無矯揉造作的自由奔放的強烈表達,獨特的隱喻,對傳統規範的突破,所有這一切使人們相信,荷爾德林是一個先驅者並且承認,他是他開創的表達藝術的早期完成者。自從諾爾伯特·海林格拉特於1916年出版了荷爾德林後期詩作的劃時代的詩集,他的詩歌的吸引力愈益強烈。二十世紀的偉大抒情詩人,從裡爾克到克蘭,荷爾德林理所當然地名列首位。
如果人們審察荷爾德林學生時代寫作的詩歌,以及從1806年至1843年他逝世這漫長的精神錯亂歲月裡寫作的詩歌,人們會發現,荷爾德林抒情詩的創作生涯實際上是從十八歲至三十三歲,即從1788年進入蒂賓根神學院至1803年。此後直至1806年初,也就是他作為精神病患者從霍姆堡到蒂賓根度過的時光,期間所創作的作品,因為缺少準確的日期標注而難以確認——還有大量的草稿、片段,以及有署名的並部分經過修改的早期斷片。
抒情詩歌創作的階段性是十分明顯的。中學時代的詩歌(1784—1788年),幾乎還沒有詩的價值,但對於理解他在一個虔信宗教的特定環境裡所受到的早期影響卻富有啟發性。它們表達了在鄧肯道爾夫和毛爾布隆修道院學校裡遭受的與生命敵對的緊張和壓迫,那種抑郁的孤獨感和對友誼的渴望,向內心的回歸以及遠大的抱負;這是一種唯有重回內心世界纔能樹立的抱負,他由此樹立了大詩人氣質的目標。他寫作的範本是克洛卜施托克,以及哈因本特,舒巴特和早期的席勒。他寫作的是世界的痛苦和廢墟詩,恰如它們在感傷主義時代廣泛傳播的那樣。
這條線在1789年仍在延伸,在蒂賓根神學院的**年,荷爾德林與其他符騰堡修道院學校的畢業生一起,進入蒂賓根神學院學習神學,直到1793年底,其中有黑格爾和謝林。然而早在1790年,一部分有共和主義傾向的神學院的志同道合者就熱情澎湃地歡呼法國革命,並且接觸了康德的批判哲學以及剛剛興起的對希臘文學和哲學的狂熱熱愛,形成了一種新的局面。這也對荷爾德林這一時期的詩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所謂的“蒂賓根頌歌”歌頌了革命的、解放的人性理想:自由、平等、博愛。那從政治、社會以及精神的枷鎖的奴役下解放出來的“人性”——《人性頌》是這個時代的代表作,表達了這個巨大的願望。這一“人性”思想也包含在18世紀流行的宇宙和諧的觀念範圍內,席勒的《歡樂頌》為此提供了創作的模本,尤其是在《和諧女神頌》和《愛情頌》中得到了表達。所有這些韻律頌歌(Reimhymne)都莊嚴宏偉,有一個理想化的抽像的基調,它遠遠高於並且避開了具體的和實際的要求。荷爾德林因此處在一個*大的氛圍裡:奧皮茨在他的《德國詩歌》中把抽像的和神秘主義的概念稱作為頌歌的對像,這一類的頌歌——歌頌孤獨、歡樂、永恆等等的頌歌(Hymne)立即在18世紀的*後十年被人們喜愛。在這種格律約束的**和韻律形式上,荷爾德林在青年時代首先把席勒作為榜樣:這個榜樣伴隨他度過了蒂賓根神學院的時光,直至他參加工作(荷爾德林受席勒的**在瓦爾特斯豪森的夏洛特·卡爾布斯家裡擔任家庭教師),以及後來在耶拿和紐爾廷根度過的時光(1794—1795年)。*鮮明的是在鬥士——英雄崇拜詩歌創作中采用了席勒式的倫理和**。他的範例是道德英雄海格力斯。早在1793年出現的頌歌《勇氣的守護神頌》就已經表明了這一點,早期頌歌中*重要的是《命運》(1794年),在法蘭克福生活時代開始時的《致海格力斯》是具有標志性的作品。由此荷爾德林達到了一個邊界,在這個邊界上他必定感受到了他的**不同的異己的敏感性。在1798年出現的頌詩(Ode)《眾人的喝彩》中,他已經自覺地尋找他自己的真實的詩歌類型,早期他接受的外部特征是空洞的**:
我的心自愛以來,已不再神聖,
向往美好生活?你們曾關注我,
因為我高傲狂野,
言辭豐富而內心空虛?
然而蒂賓根時代的韻律抒情詩帶來*初的詩的自我感覺和*初的承認:施陶特林在他的《1792年繆斯年鋻》發表了這翰·哥特羅布·施奈德的《試論品達的生平和寫作》(斯特拉斯堡1774年)”。狄俄尼西烏斯指出了冷峻的風格的識別符,那也正符合荷爾德林後期抒情詩的特點。狄俄尼索斯表征著一種冷峻的風格,它也與荷爾德林後期的抒情詩相符。他在論文《論詞語的連接》中寫道,“冷峻風格的特征如下:它致力於使詞語牢固地固著於強有力的位置,因此在所有的頁面上每一個詞都清晰地凸顯;接下來由停頓引起的各部分的分離便鮮明可見。它不畏懼經常使用粗糙和開裂的銜接,如同用揀來的石頭堆砌房子時出現的情況,它們不那麼嚴絲合縫,條理有致,而是凹凸不平,齜牙咧嘴。它常常並且喜歡出現在突展的詞語空間裡。(……)至於句子成分,它所致力的,就是使它具有雄壯華麗的節奏;它*不是雷同的或者相似的或者在一個模子裡套印的,而是孤傲獨立,光耀奪目的成分。它們不應被看作藝術而是看作自然,不應被看作因循守舊而是**充沛。它組建套疊的長句時,不讓它們把所有的思想內容都包羅其中。但是如果偶然踫到這種情況,它將強調這純屬不由自主,並非有意為之,其中既不用使句子完整、而對意義無益的補足詞,相反地為了使誦讀的節奏圓潤和平滑,還要正確地進行分割,讓朗誦者有足夠的氣息(……)此外,這一風格(……)還須有人物的豐滿度,它少有交織的聯繫,不喜歡用冠詞,不顧及自然的次序,它與纖巧細膩截然不同:它獨斷專制,自覺自立,不塗脂抹粉,具有古典的力量美。”認為狄俄尼索斯是這種冷峻風格的樣板的有品達、埃斯庫羅斯、修昔底德。
一個暗示豐富得近於高深莫測的、承載了歷史和神話的圖像世界(其在後期的抒情詩中與“回憶”的**密切相關),進入了這種剛性並且常常高度復雜的連接。它們是從1801年起頌詩和頌歌的晚期風格的主要標志。思想內容常常不再袒露無遺,而是閉鎖於豐富的符號之中。現在說“符號”這個詞是關鍵詞並非虛妄。
很難確定荷爾德林在多大的範圍內接近這種詩的處理方法,這種近乎封閉、被稱為“黑暗詩人”、“朦矓詩人”(poeta obscurus)的傳統。這種類型自古代就已經形成,它早就有一個先驅者赫拉克利特,他對於荷爾德林久已十分重要並多次引證他的理論,他就背負著一個“黑暗”的外號。對於羅馬人來說,佩爾西烏斯(Persius)就是個不折不扣的朦矓詩人。在德國文學中,哈曼(Hamann)曾經用十分矯揉造作的手法承襲這個傳統。從1801年至1803年的荷爾德林後期頌詩和頌歌,這種類型的兩個久已固定的基本元素同樣具有決定作用:一個是被**所激發的表情,其在**情況下屬於預言,另一個是打上高深的知識印記的展演,其在另外的**情況下導致難解之謎。這兩種基本元素的混合正對應了兩種類型詩人的結合:預言家型的詩人(poeta vates)和學者型的詩人(poeta doctus),朦矓詩人即屬於這類詩人。其中之一的黑暗原則上是情緒型的或衝動型的,因為它出自靈感,而另一種的黑暗則是理性的,因為它出自符號或被封閉地嵌入的知識的豐富。
經過1799年**實驗性地創作頌歌《如同在節慶的日子……》之後,於1801至1803年出現的頌歌,在風格上和建構上都決定性地模仿了品達。從品達那裡移植過來的元素,其中*重要的有雄偉的、以宏大的場景開場的序曲,它們可以在荷爾德林的頌歌《如同在節慶的日子……》、《在多瑙河之源》、《漫遊》、《和平慶典》,以及《帕特摩斯》的第二和第三節找到,而在品達則可以在第七奧林匹亞繫列、第六涅莫希斯繫列,首先是在*初的玄奧頌詩中找到。這種宏大的開篇——品達有步驟地在他的第六奧林匹亞頌詩中采用了它的功能——其任務是,創造一種歡樂喜慶的、增強莊重性的、幻想的**的氣氛,它燃起詩性的思想並通過這首詩承擔起這一任務。“想像的旅行”的結構組成的元素也發揮了特別的頌歌的作用。品達的第六首奧林匹亞頌詩提供了這種特別重要的樣板。在《漫遊》中,在《帕特摩斯》中,以及*多其他的頌歌中,還有在頌歌式躍動的悲歌《面包和美酒》中,荷爾德林以宏大的風格運用了這種藝術手段。想像的旅行是詩的靈魂把地點和時間結合起來的獨立自主性的表達。它證明了他對所有此處和現在突破者的靈感的幻想的力量。荷爾德林還從品達那裡借用了所謂的“引導的過渡”。它並非線性——邏輯的,而是聯想的,並且因此以跳躍式的、同時也是黑暗和充滿未解之謎的崇高頌詩(“頌歌”)作為典型標記的。
因此僅僅列舉荷爾德林後期頌歌中具有品達元素的作品,那些屬於**奔放、大幅度奔突激蕩的範圍的作品,是片面的。它們與屬於簡潔俗套的言簡意賅的範圍的作品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屬於這一類的有同樣出自品達的“格言詩”,它們敘述簡明扼要的觀點,如萊茵頌歌的第46行:“源出清純者是一個謎”,或者頌歌《帕特摩斯》的開篇:“哪裡有危險,拯救者|亦在哪裡生長”,或者《摩涅莫辛涅》的中心內容的簡潔的詩的表達(**2行):“可總有|渴望在無拘無束中尋找”,或者在《懷念》的結尾:“可是詩人創造的,卻永世長存”。對中心內容的概括要**有效,取決於這種格言詩的鮮明的抽像性,這種抽像性造成了與神話的形像性和大膽的隱喻的鮮明對比,也常常造成了頌歌引人注目的強烈的地理和歷史的具像性。這種詞語的靜止不動和緊密性與大型頌歌自始至終的洶湧澎湃也形成了反差,在這種洶湧澎湃中荷爾德林詩歌富有鮮明特征的凱歌行進般的軌跡直入雲霄。這一類由單純的警句或純粹的常用名言(某種參照席勒的名言)組成的格言詩所區分的是:它們不是按照大眾的理解力用相應的形式呈現淺顯易懂的東西和思想內容,以此造成“流通的硬幣”那樣討人喜歡的效果;它們*多的是詩歌中貫穿始終的精神運動的難以測度的集中,一種思想和經歷的壓縮大於其公開地袒露,其在格言詩寫作中即已保留了對讀者的挑戰和要求。尤其是荷爾德林按照品達的模式構建了他的後期頌歌。品達的勝利之歌都是三段式結構的:在首詩節後面跟著一個反詩節,在這個反詩節後面是一個有獨立韻律的第三節(終曲“Epode”)。這種三段式的結構常常可以隨意復制。品達的頌詩常常有三個、四個、五個甚至*多個三段式。按照朗薩爾把品達的頌詩作為中介模式的做法,這種三段式結構在德國巴洛克時代的品達式詩歌中是典型的,運用這種結構的有奧皮茨,格裡菲烏斯和其他很多詩人。奧皮茨在他的《德國詩論》(1624年)中對這一結構模式進行了詳盡而規範的闡釋。十八世紀戈特謝德追隨他,並在他的《批判的詩歌藝術》(1730年)中對這種結構模式進行了抽像的闡述,然後又舉例使之明白易懂。蔡特勒的百科辭典1740年版在《頌詩》條目下逐字逐句地照搬了戈特謝德的闡述,品達的結構模式的知識已是規範的認知,它已經變得如此不言而喻,該詞典自那以來的大的版本中關於品達的頌詩詩節都用“首詩節”、“反詩節”和“終曲”作標記。因此荷爾德林已經處在一個品達知識和品達詩歌的既定的傳統之中,所以他幾乎所有的後期詩歌(其中***的《日耳曼尼亞》和《懷念》)都以品達的三段式結構進行了構建。
由於這種三段式結構常常可以隨意重復,所以已經有可能以品達式頌詩的模式創作出極力向外擴展的抒情詩作。它允許作品的史詩化(這在荷爾德林的一些頌歌中也可以清楚地辨認出來),但也迎合了巴洛克的**昂揚的需要,或者克洛卜施托克和青年歌德的主題獨創的情感需求。在這方面也有所保持的荷爾德林首先感覺到了品達式的“崇高頌詩”(hohen Ode)的伸展的廣度,因為它給擴展的唯心主義繫統學和不斷伸展的詩性思維的透視深度提供了一個經過測量的空間。
荷爾德林根據結構模式安排一個三段式的三個詩節內的詩行數目,以及各個三段式相互之間的比例,但是偶爾也有偏離;在頌歌《如同在節慶的日子……》進行*初嘗試之後,他放棄了從頭到尾使用韻律的創作方式。這種自由在文藝復興以來的品達式頌詩中已經成為傳統。荷爾德林的後期頌歌都是不受韻律約束的、無韻律體的頌歌,這種頌歌從克洛卜施托克和青年歌德的狂飆突進以來已為人們熟知。
荷爾德林為他的後期頌歌采用品達的形式進行了結構構建,以此他站在了一個歷史的延續中,這比昆提利安根據準則構建的原則評價品達為所有抒情詩人之翹楚、作為“首席抒情詩人”(princeps lyricorum)*具有決定意義——這一評價*早反映在荷爾德林的碩士論文《希臘人的美的藝術史》中,在該文中他贊揚品達是“詩歌藝術的集大成者”。從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朗薩爾的《品達式頌詩》延續的品達化詩歌創作的悠久傳統,在德國經由奧皮茨延伸到十八世紀,對荷爾德林的後期頌歌采用品達形式起到決定作用的是,“崇高頌詩”(現代用語:頌歌)的理論已與品達緊緊地聯結在一起:他的後期頌歌立足於一個在分類理論上已經深深打上品達印記的境界裡。尤其是在十八世紀,品達的詩歌創作風格已由霍拉茨的**的品達——卡門(Carmina:頌詩) **地確定為**天然的、無規則**的“崇高頌詩”。克洛卜施托克在他1747年面世的《致友人》中論述了這種品達理解(verst?ndnis),此後很多人仿效他。作為希臘藝術的專家和翻譯家,荷爾德林憑一己之力要**掌握品達也並非易事;他使一個在本質元素上早已預先塑造好的品達接受(Pindar-Rezeption)以及一個“崇高頌詩”的相應理論*多地具有現實意義。盡管他並未承襲天纔時代的矯揉造作的非理性主義,可是他對品達的興趣卻首先由不斷的嘗試所證實,他試圖尋找一種詩歌言說的非傳統形式。在《和平慶典》的前言中綱領性地談到了一種諸如非“傳統的”,而不是“自然”生發的詩作。後期頌歌找到了這種形式。
對於荷爾德林來說,品達始終是一個突破傳統的違背常規的傳統。它要求一種**自己的、決非古典地模仿希臘的詩的表達方式作為中介;要求一種荷爾德林稱之為“祖國的”和“自然的”詩的語言作為中介。他在給波倫道爾夫的第二封信中談到了他的意圖:“歌唱祖國的和自然的、**新穎的”。1803年9月28日在給他的譯作的出版人弗裡德裡希·韋爾曼的信中說,他現在能夠“比過去……*多地出於對自然的和*多的對祖國的感受而寫作……”。荷爾德林在1803年12月給韋爾曼的信中提到克洛卜施托克,他找到了一種經常提及、但並不理解的“崇高和純粹歡樂的祖國之歌”的表達語言。這種表達語言隻有在頌詩理論的歷史背景下纔能理解。
“歌”這個詞隻是希臘語詞“頌詩”的字面翻譯。“歡樂”無非是指在崇高的、品達式頌詩理論中牢牢扎根的**概念,但不是某種歡騰——*多的是崇高靈感和上升的精神經歷之聲,它一直上升到幻像之中。在頌詩理論中它長久以來都屬於“崇高頌詩”的嚴格規定,即它們必須是發自內心的熱情。它與使“崇高頌詩”成為頌歌*純粹形式的強烈的緊張度的想像合為一體。然而荷爾德林談到的並非僅僅“純粹的”,而**首要的是這種歌的“崇高的”歡樂。他這樣說並不是以隨意的和個人的方式指稱上述詩歌創作方式,而*多的是抓住了十八世紀美學的關鍵概念:崇高的、高度的概念。它來自於十八世紀假冒的朗吉努斯的正式經文篇章《論崇高》。
由此抵達了實質上的美學境界,其中有“崇高頌詩”的類別,荷爾德林的後期頌歌也在其中。朗吉努斯把崇高理解為心靈越過常人的尺度而升騰的興奮劑。崇高即越過日常的現實而進入理想的王國,就此而言它屬於一個特殊的唯心主義的詩歌創作。朗吉努斯如是說,自然,荷爾德林做過充分的研究(可由瑪格瑙於1788年7月10日給荷爾德林的信中得知),自然對人的規定無非是要對整個宇宙進行觀察;自然用一種對偉大和神性無法克制的渴望來滿足人,以至於人的思想努力**圍繞著他的世界的邊界。這就解釋了他為什麼對涓涓細流不感興趣,盡管它清澈有用,而是著迷於多瑙河和萊茵河。朗吉努斯要求詩歌必須具有宇宙的寬廣和偉大的要求,沒有一個詩人能夠像荷爾德林這樣全面地符合,如果人們撇開克洛卜施托克的仍然抽像的經驗不談的話。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後期頌歌的一個主要識別符是一種無畏地越過國土和海洋以及歷史時空的想像的力量。朗吉努斯對廣大的自然現像、主要是浩浩蕩蕩的河流如萊茵河和多瑙河的詩意的知性的概述,已經頗具創意地導向了荷爾德林的後期頌歌——導向了頌歌《萊茵河》,《在多瑙河之源》,《伊斯特河》。對於他,可以屬於“崇高”的首先是向著“神性”領域的升騰,以及向著他*近的、**常人的尺度的“英雄”和“半神”的領域的飛升。他們由荷馬的偉大英雄作為代表,對他們的記憶是他*後的頌歌《摩涅莫辛涅》,當然還有狄俄尼索斯、海格力斯和基督。頌歌《**者》正是獻給這三個“半神”形像的,在*多的後期頌歌中他們都同樣直接或間接地具有結構構建的意義。按照“崇高”的標尺,後期頌歌屬於這一標尺劃分的還有在歷史中離得較近的神性化的人物,例如在萊茵頌歌中的盧梭,荷爾德林在題獻給他的詩節部分用了獨特的詞語:“現在我思考的是半神。”
詩意的想像力向著至高處的飆升,*終與荷爾德林把自身作為詩人安置於“崇高”的領域相符,尤其是當他的詩意的想像力對此傾注之時。這已偶然地發生在一幅幅圖片般的想像之域,是某種他在《摩涅莫辛涅》中讓那個“漫遊之人”在阿爾卑斯山的“高路”上,當他朝著一個方向孤獨地俯瞰時,向著遙遠的過去回眸時得到的景觀,而這個漫遊的人如同過去一樣也是詩人偏愛的代碼。但首先這個代碼在詩人向至高處上升的使命和形像中顯現出來;也在詩人的悲劇中顯現出來,在悲劇中他認為自己等同於“英雄”,如同在頌歌《**者》和《摩涅莫辛涅》的結尾處那樣。
眾多的法語和英語文章探討崇高的問題,其中埃德蒙德·伯克的《我們關於崇高和美的哲學探討》(1757年)*具特色,在德國,有波***和布賴廷格爾,克洛卜施托克,鮑姆加爾滕,英澤斯,孟德爾松。關於崇高的理論,直至康德的《關於美和崇高的感受的觀察》以及他的《判斷力批判》(第二卷**分冊第二部分):《崇高分析》,席勒的論文《論崇高》,一直延續到後來的赫爾德及*終的謝林。由此十八世紀的一個基本進程就可以理解了,這也是荷爾德林參與的,也就是試圖把宗教所失落之物以及在理論上不思考的抽像物從美學上予以體現。對於席勒來說,崇高服務於促成理論的理性正在擺脫的超驗性。當批判理性的傳統形而上學墮落成為犧牲者,崇高應當通過“溫柔情調”的感染作用再現這種形而上學的對像,因此崇高之物成為了一種**違背理性地予以規定的觀念的記號,它標明了一種在世俗化的理性闡釋壓力下出現的情感需求。這在德國音樂和文學中,在席勒,貝多芬和荷爾德林那裡,找到了它*高昂的**。而對於謝林來說,在1800年發表的《先驗唯心主義體繫》中,崇高是在有限之物中對無限之物的幻覺。
至於這種詩的體征,在荷爾德林這一代趨於完整的唯心主義形態的崇高,在克洛卜施托克那裡已經出現,在他1755年面世的《彌賽亞》**卷的前言(標題為:《論聖詩》)中以及在論文《論詩的語言》中,已經作為主題多次論述了崇高,崇高性,甚至論述了詩的“高度”並以此直接影射了朗吉努斯的“Hypsos”(高度)。克洛卜施托克的詩作從繃緊的狀態平淡地擴張到高度和極高度。因此,荷爾德林在1803年致韋爾曼的信中談到了“祖國之歌的高度的和純粹的歡樂”,並直接在這些詞語之後提到了克洛卜施托克的《彌賽亞》,也就不足為奇了。
從上面討論唯心主義的意義上,不僅有荷爾德林的後期頌歌,還有他的很多頌詩以及一些悲歌都在“崇高”的境界中,甚至在抒情的風格樂觀高昂的《許佩裡翁》也如同在標題的提綱中——“許佩裡翁”,自從荷馬為太陽神取了這個外號,用德語說是:“凌空而過者”——“高度”,“崇高”的**觀念就生效了。因此,後期頌歌以特殊的方式代表了“崇高”詩歌的類型。因為從那以來“崇高頌詩”的理論,如*近的規定已表明的,已固定於“高度的”崇高之物上。頌詩理論已經把崇高的理念與品達式頌詩結合在一起。美學的**觀念和文學的模式就這樣為荷爾德林在傳統中融為一體,而這個傳統是他自覺地遵循的。自從十七世紀以來,人們緊隨著古代修辭學家們的分析,把“小的”、阿納克利翁風格的頌詩與“宏大的”、“高度的”品達式頌詩作為相反的類型區分開來。如果說品達式頌詩宏大、**澎湃、崇高、激越、自然且不受規則約束,那麼阿納克利翁的頌詩則小巧、優雅、平和且循規蹈矩。品達式頌詩偏愛神、英雄、自然的壯觀景物如風暴、江河、大海和山脈,阿納克利翁頌詩則拘泥於愛情和美酒,喜歡小小的鄉土的滿足和輕松的品味(對這種類型的頌詩,荷爾德林在給韋爾曼的信中,談到了“愛情歌曲”的疲憊的飛行)。尤其是品達式頌詩具有黑暗和深奧的特點,而阿納克利翁頌詩則明白易懂。在**的辭書中有關頌詩的文章說明了頌詩理論的這種基本結構如何堅不可摧,這類辭書有狄德羅和達朗貝爾合編的《大百科全書》,舒爾策的《美的藝術通論》。*重要的,構建了延續到十八世紀末的頌詩規範、考慮到了崇高觀念與頌詩中品達模式的特殊結合的理論家是布瓦洛和他的《詩藝》和《頌詩的語言》(1693年)。
同一個詩人作品與作品之間的差距,並不比荷爾德林高度緊張的後期頌歌與他在蒂賓根塔樓中度過的漫長黑暗歲月裡寫下的詩之間的差距*大,這是可以想像的,在那些歲月裡,來訪者請求他寫幾句詩,這種情況並不少見。在一些甚至*長維度的構成物之後,是一種持續的、特有的松弛的、單一的詩行,然而在它們的簡單中有時也會有讓人激動的詩句。總是相同的風光想像,那是這位詩人從他居室裡越過內卡河向當時還未被遮擋的河邊草場、向地平線上的施瓦本的阿爾卑斯山眺望時的即景,還有,總是一年四季。固定不變的圖景,老一套的同時也是透明的詞語,表達某些沒有說出來的、說不出來的東西。沒完沒了地呈現著在世界與一個面對日益消蝕的時光恐懼地回撤的自我之間的距離,這個我*終仍被隱沒在一個假名的後面。起先常常是半催眠狀態決定著詩句的語言,現在幾乎僅有*簡單的並列結構,以彩色花環一環套一環的鏈接,於是詩行的統一性和思想的統一性都倒塌了。縮減和退行成為單調獃板的自然景物的特征,它們不再生氣勃勃,而是如同用同樣的基本材料在沙箱遊戲中塑形那樣僵化不變。現在已消失很久的韻律以*簡單的形式重新出現,幾乎是全自動地發生,如同幽靈般儀式化地和諧協調,它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魔法般地召入諸如“照耀”、“晴朗”、“華麗”等詞彙之中。荷爾德林仍然鐘情的、**藝術的概念是典型的“和諧”和“**”。此種源自倒塌中的反射與一種非現實性相對立,在這種非現實性中,世界與人已經疏遠至“圖像”——*常用的這個詞就是這麼說的。荷爾德林詩意地預見到他的語言和他的存在的這一結局,他在*後的頌歌《摩涅莫辛涅》的初稿中寫道:
我們隻是一個符號,毫無意義
我們也無痛苦,並幾乎已把
語言遺失在陌生之地。
位時年22歲的青年的首批詩作,不久又有*多的作品發表。*初的詩歌成就增強了荷爾德林把詩歌創作作為職業的展望;背棄神學的決心已定。
告別蒂賓根的時間即是《許佩裡翁》(Hyperion)的開始。從1794到1799年,除了作為謀生手段的家庭教師的工作之餘,他集中精力於其上。席勒於1975年3月9日向科塔**出版《許佩裡翁》並把小說的片段在自己的雜志《塔利亞》(Thalia)上發表,這必定鼓舞荷爾德林頑強地繼續創作這部小說。因此,直至《許佩裡翁》**卷出版(1799年)的這幾年裡,抒情詩的創作比從前少了;可是通過《許佩裡翁》的寫作,給作者敞開了一個廣闊而豐富的詩的表達的前景,沒有這項工作,那麼《許佩裡翁》之後發表的抒情詩作品是不可想像的。還要提到鋻於小說的種類,在《許佩裡翁》中以一種不同尋常的尺度注入了抒情的能量。
在法蘭克福時期(1796—1798年),也就是與蘇賽特·龔塔爾特陷入愛情的時期,她被荷爾德林詩性地、理想化地稱為“狄奧提瑪”。他在一段短時間內保持了“詞語豐富”的多段式韻律頌歌的形式,如在現存的多個稿本的韻律頌歌《狄奧提瑪》中的情形。在精神上也促使早期的詩作延續下去,因為此時狄奧提瑪已成為他本人的普遍的宇宙和諧的代表,這種和諧此前曾創作了偉大的韻律頌歌《和諧女神頌》。盡管此後數量很多的《狄奧提瑪》詩篇激勵了一種語調深沉,豐富並充滿活力的情感,可是如同在《許佩裡翁》中一樣,狄奧提瑪在此仍是由精神境界構畫的:由溫克爾曼的經典希臘觀,即可在套語“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中找到的表達式,以及柏拉圖的理想主義升華的阨洛斯觀(Eros-Konzeption)。柏拉圖在《宴飲篇》中創造了阨洛斯觀這個詞,狄奧提瑪的名字即來源於此。
不久荷爾德林就放棄了從法蘭克福時期保留下來的韻律頌歌的形式,而選擇了**不同的行和節的形式。他寫作六音步詩,如《致以太》,**首悲歌(Elegie)《遊子(**稿本)》,一首無韻體詩《人民沉默,沉睡……》,他還實驗了自己的形式,如《許佩裡翁的命運之歌》;但他首先掌握了作為頌詩詩人的精湛技巧。從此直至他創作的結束,他開始了不斷豐富的抒情詩種類的持續拓展,在這方面他遠遠超過了***的德國詩人。在中學時代的詩歌中荷爾德林就已經有幾次嘗試頌詩創作並運用了雙節的頌詩詩節,而從現在起他選用阿爾開俄斯體和阿斯克勒庇亞迪體頌詩,隻有一個***的例外,即薩福體頌詩《在阿爾卑斯山下歌唱》(1801年)。古典的詩和18世紀的詩,以及克洛卜施托克的詩,尤其是霍拉斯的爐火純青的詩作,對他有決定性的影響。
在法蘭克福時期荷爾德林幾乎隻寫短的頌詩,它們至多隻有兩至三個詩節,與此前洋洋灑灑的長篇韻律頌歌明顯地背道而馳。現在荷爾德林恪守簡潔的型式,簡練明晰的詞語風格,以及扼要明確的表達方式。這也是迎合歌德的忠告,“寫短詩並為每一首詩選擇一個人們感興趣的題目”(據1797年8月23日歌德致席勒的信);席勒也在1796年11月24日給他的信中提議,不要失落“**中的冷靜”,避免“冗長拖沓”。
阿爾開俄斯體頌詩的詩節形式如下:
∪-∪-∪|-∪∪-∪- (阿爾開俄斯體 11個音節)
∪-∪-∪|-∪∪-∪- (阿爾開俄斯體 11個音節)
∪-∪-∪-∪-∪ (阿爾開俄斯體 9個音節)
-∪∪-∪∪-∪-∪ (阿爾開俄斯體 10個音節)
阿斯克勒庇亞迪體頌詩的詩節形式如下:
-∪-∪∪-|-∪∪-∪- (阿斯克勒庇亞迪體)
-∪-∪∪-|-∪∪-∪- (阿斯克勒庇亞迪體)
-∪-∪∪-∪ (菲勒克拉特體)
-∪-∪∪-∪- (格萊坎體)
兩種詩節的形式總的來說都是首兩行結構相同,區別在於後續的詩行,即首兩行較大的詩行通過一個停頓連接後續的詩行——後兩行較短且沒有停頓。這一格律照應到了既充分又有區別的表達效果。阿爾開俄斯體詩節的頭兩行,在停頓處緊跟著抑音節有一個揚音節,這樣由於停頓處沒有句法的缺口,這行詩在相同的起伏中越過界限。首行中前後兩部分的情況也適用於整個詩節:揚和抑的起伏(或者抑和揚)從這一行的末尾到下一行的起始保持得很好。但是阿斯克勒庇亞迪體的情況**不同。不僅在頭兩行的停頓處,而且在行的末尾揚音節總是互相衝撞:這就產生了所謂的“揚音節衝撞”。阿爾開俄斯體的詩節,其向外擴展的波浪運動柔弱並流動,而阿斯克勒庇亞迪體則由於其揚音節衝撞在首行和其內部不斷返回,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結構:它把單個的行與該行的組成部分**地對立起來。當然,這兩種詩節形式不同的結構僅在理想的典型的地方纔能顯出效果,例如句法的和邏輯的成分被韻律所覆蓋,如在《蘇格拉底和亞西比德》這首阿斯克勒庇亞迪體頌詩的*後一節:
誰研思*深奧,就愛*活躍者,
誰觀察世事,就懂得青春高貴,
智者常常在*後
向美好的事物致意。
荷爾德林在法蘭克福時期(不是全部,但是相當長的時間內)把他的頌詩體詩作限制於短頌詩,此後他重又創作長詩並一發而不可收,不僅在頌詩(這他一直堅持到*後)的時期,而且還在悲歌時期及後期頌歌時期,都是這樣。現在他常常寫作大型的、長詩節的頌詩,並且把法蘭克福時期創作的一繫列短頌詩擴寫成大型的頌詩。
觀察法蘭克福的兩年,不僅《許佩裡翁》取得了決定性的進步,而且精湛了頌詩的創作,它們從精神上引導進入了這樣一個境界,從現在起它決定性地形成了:荷爾德林形成了由他同時代的斯賓諾莎主義所激勵的泛神論的世界觀,其中融入了由盧梭推崇的對自然的崇拜,其主要的證明就是《許佩裡翁》。但是也在詩歌中找到了這種泛神論世界觀的強烈的表達。這種世界觀在六音步抒情詩(Hexameterhymnus)《致以太》中得到了全面繫統地(仍有一點是圖表式)的展示,“以太”是斯多葛主義——泛神論的主要像征,這統攝一切並使一切具有靈魂的自然力的標志出現在了標題中。直至1800—1801年的那些宏大詩篇裡,《阿奇佩拉古斯》,以及悲歌《面包和美酒》,《還鄉》,“以太”這個泛神論的符號已深入其中。被神化的以太預示了自然的新的神性。是的,這種關於“神性”的談論,**源出於自然的神聖性,是作為一切生命承載和合法性的理由。這一“神性”的談論決非指天國的神性。它拒*超驗的斷然,重新評價的堅決,取回此前超驗在“自然”的內在性中添加的品質,這在短頌詩《瓦尼尼》中清楚地表現出來,它也是短頌詩達到高峰形式的一個典範。
在必須離開龔塔爾特的住宅之後,荷爾德林自1798年9月至1800年6月留在法蘭克福的附近:霍姆堡,在那裡有機會時他可以跟他的情人見面。應朋友辛克萊邀請,荷爾德林與霍姆堡的侯爵家庭建立了聯繫,辛克萊就在他家效力。兩首頌詩《致霍姆堡的奧古斯特公主》和《致德騷的阿瑪莉公主》與霍姆堡宮廷交往的生活圈有關,它們都出現在1799年秋天。與蘇賽特·龔塔爾特分離和告別的痛苦在一繫列愛情詩中表達出來,其中於1800年初夏從《悲歌》中產生的大型告別悲歌《梅農哭訴狄奧提瑪》和頌詩《離別》屬於德國文學中***的詩篇。
生活不幸的陰影變得*加深重,他想出版一份文學雜志以獲得牢固的生存基礎的計劃破滅了。他原想通過這一計劃把自己從居無定所、有失體面的依附性的家庭教師的職業中解放出來。與雜志的出版計劃有關,他還設想了自己為雜志撰稿,為此出現了*多詩歌理論的論文——這些論述詩人的題目現在詩歌中也有**重要的位置。首先它們反映了詩人承受的命運。它似乎是悲劇性的,因為它讓詩人疏遠了一切人的生活聯繫。這種疏遠的悲劇感,孤獨感,遺棄感,在兩首同樣真實感人的頌詩《傍晚的幻想》和《我的財富》中表達出來。這些“歌”成了詩人自身的“避難所”,成了詩人**的“幸福”,因為他始終被隔*於人生的幸福。即使在《詩人的勇氣》這樣看上去**積極地吟唱的詩歌裡,也能感覺到痛苦的失落感。詩人試圖在這首詩中說出自己的勇氣,他在生命聯繫實際上被閉鎖的地方想像一種先驗的生命聯繫。
另一方面,荷爾德林在詩歌中,也像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一樣,特別是同一時期出現的悲劇《恩培多克勒》中追隨一種趨勢,即**主體、個體和自身,他以此來謀求詩人身份的合法性。這以一種引人注目的方式發生在他*早的晚期頌歌《如同在節慶的日子……》之中,以及在離開霍姆堡之後很短的時間裡出現的《詩人的天職》之中。始於霍姆堡時期的詩人自身的內省,一直到精神崩潰的前夕,始終是荷爾德林詩歌的基本特征。人們稱他為“詩人之詩人”並無不合理之處。
這種對詩人身份合法性的內省,與他客體的任務的規定性結合在一起。荷爾德林把這種規定性看作為一個統一語境的精神媒介,這個統一的語境被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神秘地描述為“神性的”,他坦誠地把它看作為植根於(從泛神論的意義上理解的)自然的生活。從中產生了他的兩個前景。一是他用誘發力開發了一種“文化”的觀念,它源自於和諧的人與“自然”普遍的生活聯繫之結合。例如他認為此種結合已經完成,此種眼界並不是要像古典主義者那樣從美學上模仿希臘人,相反,他反復地向他同時代的人栩栩如生地想像希臘文化。他在強大的六音步頌歌《阿奇佩拉古斯》以及在1800與1801年之交出現的、他*優美的悲歌《面包和美酒》中,*充分地闡釋了這種聯繫。其二,他期望,德國召喚這樣一種文化的出現,盡管在《許佩裡翁》裡大聲責罵了那些野蠻地疏遠自然的行為,它畢竟還是存在於正在上升的德國人專家一樣的、各不相同的日常作為中。他一度滿懷**地歡呼法國革命,並長久地追隨它的理想,但它的後續進程卻讓他失望,他不再相信人性會從法國獲得新生。當革命在法國崩潰之後,他把進化作為德國走向歷史完成的道路,並把一個自然—統一性的概念理想化地與進化的歷史模式結合起來。盡管德國在政治上無能,但是在十八世紀的*後十年培養了一種充滿期待的文學的和藝術的生活,與其他同時代的人一樣,荷爾德林也認為德國在*廣泛的意義上實現文化完成是可能的。為此他於1799年創作了頌詩《德國人之歌》;兩年之後,1801年末,出現了頌歌《日耳曼尼亞》,它承載了同樣的期待,在德國發育一種根源於自然的、統一性的文化。
那並不意味著荷爾德林觀念狹隘且**否認政治。他對時事表現出過於強烈的關注,並在事態發展到高峰時,他又會再次考慮革命鬥爭。所以在霍姆堡時期出現了在詩意上無足輕重、但政治上卻富於啟發的頌詩《為祖國而死》。那個時期的詩作都表明,荷爾德林在與他具有相同觀念的霍姆堡的朋友圈子裡,是多麼密切地關注時事,盡管他把其中的大多數都抬高到一個虛無縹緲的幻境中。1799年5月朋友波倫道爾夫描寫霍姆堡的辛克萊和荷爾德林:“我在這裡有一個朋友,一個徹頭徹尾的共和主義者,還有另一個朋友,他活在心靈和真理之中。”
荷爾德林於1800年5月8日與蘇賽特·龔塔爾特*後一次見面,此前在1799年秋他已把《許佩裡翁》的第二卷題寫了“舍你其誰”獻給她。1800年6月荷爾德林離開霍姆堡前往施瓦本故鄉,在那裡他直到年底在斯圖加特的商人克裡斯蒂安·蘭道爾的家中找到了友好的住處。一旦感覺到他詩性的存在與所有普通人生活境遇的疏遠,以及*終失去蘇賽特·龔塔爾特,反倒使他變得*容易為人所接受,盡管隻是暫時的“活在生活中”。從失去故鄉的悲劇感,這既是外在的命運,也是內在的阨運,到在斯圖加特的朋友圈子裡體驗到社交生活的加倍的親密感,他感受著故鄉的風光。從1800年夏天開始,他寫作頌詩和悲歌,其中都飽含著這種感受和體驗。故鄉的河,內卡河,他在一首詩中向她致意(《內卡河》)。在另一首詩中向“早就熱愛著的”海德堡致意,頌詩《海德堡》是他***的頌詩。還有一首頌詩題為《回故鄉》。而他的悲歌則接連不斷地快速出現,並成為這幾個成果豐碩的月份裡的一個重點。在那些悲歌裡,總是真實的故鄉從一個理想的故鄉中透射過來,它們導向一種*崇高的履職事件的暗示(Andeutung des Erfüllungsgeschehens)。荷爾德林把他在詩中提到的朋友、親人和同胞都囊括其中。從悲歌《遊子》(第二稿本)——在故鄉一次詩性的漫遊,這一基本結構一直延伸到悲歌《斯圖加特》,它如同頌詩《海德堡》,都采用了古典的、尤其是品達的城市贊美詩的模式,一直到《面包和美酒》的起始部分,以及*後的悲歌《還鄉》。這首《還鄉》寫的是1801年春從瑞士短暫留住後返回故鄉的旅程。
荷爾德林在法蘭克福時期(1796—1798年)頌詩的寫作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轉而在1800年下半年實現了悲歌創作的成熟,此前的幾年裡他僅偶爾嘗試這種形式的創作。可他在繼續創作**頌詩的同時,人們在1801年春又另外得到了悲歌《還鄉》,此時悲歌作品已臻成熟。可能在1799年就已經開始寫作的《悲歌》,他在1800年夏改寫成《梅農哭訴狄奧提瑪》,它幾乎被定義為自羅馬詩歌以來的作品,按照羅馬詩歌的標準其始終是愛情詩。在這種羅馬分類的傳統的背景上,荷爾德林選擇了《悲歌》這個簡潔的題目。此後的悲歌遵循了*開放*廣泛的希臘悲歌的分類傳統。在詩中占**的**不是狹義的“悲歌式的”,它們包含了詩的聲音和詩的表達的豐富的譜繫。是啊,“歡樂”是其中的關鍵詞。與友人一起在狄俄尼索斯式的光艷明亮的風景中燃燒**的火焰是這些詩的基線。其大幅度擺動的悲歌式錯落雙行的詩節(Distichon),有英雄史詩的傾向,極易於形成一幅幅逼真的圖像及個人的特性。有時候故鄉的風光會有全然舞臺劇的品色。然而悲歌的生命在於色彩絢麗的印像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之間的張力。《面包和美酒》占據了某個特殊的位置。在其他的悲歌裡,在光彩絢麗、崇高神秘的故鄉風景裡暢遊,現在變成了一種想像豐富的旅行——從狄俄尼索斯式的**滿懷的故鄉的當下進入一個截然不同的境界——以希臘為楷模的自身理想化的烏托邦。在故鄉的城市裡的傍晚和夜晚音調的高度詩性的印像,現在僅僅作為懷舊的、同時烏托邦式勾勒的心靈這種雙重運動的脈動。為此它開始了如在《阿奇佩拉古斯》中運用的歷史性記憶的空間。沒有一個詩人像荷爾德林那樣,在他1800—1803年的創作**期把如此強烈的記憶和歷史作為他詩的生命線。
1801至1803年出現的後期頌歌的大部分也呈現出這種記憶的風格,尤其是歷史的和神秘化的記憶的風格。為此常常是以品達為楷模,漫遊者的動機和想像豐富的旅行融為一體。因此後期頌歌的*早的作品都有獨特的標題,《漫遊》,《帕特摩斯》和《懷念》也是如此。*後的頌歌《摩涅莫辛涅》的標題也像《懷念》一樣,是以記憶作為主題的;記憶還確定了*多後期頌詩的主題,如《人民之聲》第二稿本以及頌詩《眼淚》和《酒童》。回憶*終成為詩作貫穿始終的結構,這一結構大部分情況下是荷爾德林全部詩作神話般地構造而成的:偉大的頌詩《喀戎》。當整個的想像在此從神話的構建中顯現,詩本身**變成了回憶者的說明,即神話的說明。
歷史在兩個主要方面展示自身。首先是在文化的漫遊之下。荷爾德林總是一再采用從古代經過人文主義直至十八世紀一直流傳下來的文化漫遊的觀念,例如在頌歌《在多瑙河之源》,《日耳曼尼亞》和《伊斯特河》以及後期頌歌的草稿《鷹》。它們就如同人類的文化史,是一個從東方到西方的漫遊。荷爾德林的期望在於,歷史的瞬間已經來到,在此瞬間,在*廣泛的意義上那曾經屬於東方、希臘和羅馬的“文化”實現,現在或將屬於德國,他自己也說,抵達了“赫斯伯裡”(希臘神話中的金蘋果園——譯者注)。頌歌《面包和美酒》,特別是後期對《面包和美酒》的深思熟慮的加工,是歷史作為文化漫遊的觀念的根據,其神話的隱喻即是狄俄尼索斯從印度向西方的行進。
其二,歷史現在似乎顯現出了目的論的一面。還在1800年時,荷爾德林的歷史觀已經變成了本質上的循環論。在他此前的詩作中他常常談到從“白晝”到“夜晚”的周期性的轉換,即從未完成到完成的時間的轉換。但是在後期頌歌《和平慶典》,《**者》和《帕特摩斯》中,歷史進程變成了線性目的論。它在一個塵世的**中趨向終點。這一塵世的**出現於普遍和解的視野中並經由“精神”作用的中介。普遍和解的神話般的隱喻是所有“神性”的形像和權力的統一,它們在歷史中作用,也超過了傳統的巨大的歷史階段,即由基督前的古代向基督時代的“時代轉換”。因此,荷爾德林稱狄俄尼索斯、海格力斯和基督為“兄弟”。澄明的容忍理念就這樣被提升到世界歷史的高度。
從泛神論把自然理解為一個所有單個的生命體經由總的聯繫而成為統一體的歷史化(Vergeschichtlichung)傾向是顯而易見的。歷史被理解為一個進步的、一切經由中介的精神化的過程。這其中也表明,荷爾德林如何執著於唯心主義的心靈——思考的境界中,盡管他在對費希特的探討中早已經以他**化的主體批判地否定了與特有的主觀唯心主義對立。對歷史哲學頌歌《和平慶典》和《帕特摩斯》中的歷史目的論進程起決定作用的,並非人的精神及其感官——草圖,*多的則是一個**客觀地轉變了的精神,它在歷史的進程中純粹是作為“世界之精神”逐漸形成的,如在《和平慶典》中所說。救世史就這樣在自然的—和精神的歷史中世俗化地轉變。
一個從文化史的角度強調的完成事件的、以及一個世界史的、直接導致消除由時間和歷史自身引導的終結事件的詩的幻像的天國,出現在精神崩潰前*後幾年的詩作中,其一直是表達的難題,人們隻能稱之為荷爾德林的獨特之處。它早已有所顯露,在恩培多克勒的戲劇中有宏大的表達,而現在,臨近結束時,上升至強烈的迫切性。這是一種向著**解放的決死的突進,要突破此在(Dasein)的邊界而出。*後的頌歌《摩涅莫辛涅》用如下的詩行表達了:“可總有|一種渴望在無拘無束中尋找。”別的詩作談到了“死亡之欲”。荷爾德林把這種決死的——悲劇性的突破邊界的衝動看作為“英雄”的“英雄狂熱”(furor heroicus),他把它與他的“詩興勃發”(furor poeticus)等同起來;但他同時也認為,它在向著集體命運的*強大的上升中,在全體人民和所有城市中起作用。與此有關的主要作品有《人民之聲》(特別是它的第二稿本),《眼淚》,《生命的歷程》和《摩涅莫辛涅》,以及後來的頌歌草稿《希臘》。
然而現在卻顯露出一種跡像,荷爾德林在感覺到來自外部的急迫性的同時,總有一種不斷迫近的、對這種突破衝動的可疑的抵抗力,與所有的狂熱相對抗。這同樣也在《摩涅莫辛涅》中——作為對這種“在無拘無束中”行進的“渴望”相對的條件反射——以及在後來的頌歌草稿《希臘》和在《**者》的第二稿本中。是的,許多此前的詩作現在正經歷一種有目標的深刻的改寫(Neufassung),要對那些慶典、法則、中介者、尺規、有限者、個性以及他自身對自然力、無邊界者、散射者,尤其是對生活經歷的直接性、感覺的過度,以及對狂熱的痴迷的強烈的覺醒,作出有力的標記。這一傾向的有決定意義的印記是把頌詩《盲歌手》改寫成《喀戎》,把《詩人的勇氣》改寫成《苦悶》。
不僅其精神的品位,而且在語言的形式上,荷爾德林後期的抒情詩也進入一種不同尋常的、**的形態。其標志是,大膽的隱喻以及抽像的剛烈,多彩的畫面,質樸的語言,大幅度擴張的、以強烈的節奏運動的大尺度時間周期,以及精煉的簡短。其*引人注目的元素之一是所謂的“剛性的連接”(harte Fügung)和“冷峻的風格”(herbe Stil)——一個概念,古代的修辭學者,哈裡卡索斯的狄俄尼西烏斯首先把它用來描述品達,而品達正是荷爾德林在*後幾年的楷模。荷爾德林自己也寫了*大的有關品達的論文,闡發了哈裡卡索斯的狄俄尼西烏斯為品達設立的風格標準:“約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