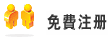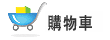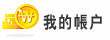昔年中原武林決戰北荒摩雲教,刀客雲荊山橫空出世,以一己之力救武林於危難,從此被尊為“天下刀宗”。十三年過去,執掌武林的正氣長鋒閣卻突然召集各派高手共赴昆侖,要誅殺隱居多年的刀宗。此時此刻,還沒有人能預料到,“籍籍無名”的山野散人吳重和他的懵懂徒弟葉涼,對萬事皆不掛心的懶散僕從陳徹和女主人寧簡,這一對師徒、一對主僕即將改變這場浩大詭譎的武林紛爭……
長篇武俠小說“天下刀宗”繫列第二部。昔年中原武林決戰北荒摩雲教,刀客雲荊山橫空出世,以一己之力救武林於危難,從此被尊為“天下刀宗”。十三年過去,正氣長鋒閣號令高手共赴昆侖誅殺刀宗。在這一部中,楊仞登場,因攜帶刀宗書入江湖,被正氣長峰閣追拿,陸續和葉涼、陳徹結識,以楊仞為幫主、與停雲書院對抗的乘峰幫也開始廣收幫眾。
長篇武俠小說“天下刀宗”繫列第二部。昔年中原武林決戰北荒摩雲教,刀客雲荊山橫空出世,以一己之力救武林於危難,從此被尊為“天下刀宗”。十三年過去,正氣長鋒閣號令高手共赴昆侖誅殺刀宗。在這一部中,楊仞登場,因攜帶刀宗書入江湖,被正氣長峰閣追拿,陸續和葉涼、陳徹結識,以楊仞為幫主、與停雲書院對抗的乘峰幫也開始廣收幫眾。
長篇武俠小說“天下刀宗”繫列第四部(大結局)。昔年中原武林決戰北荒摩雲教,刀客雲荊山橫空出世,以一己之力救武林於危難,從此被尊為“天下刀宗”。十三年過去,正氣長鋒閣號令高手共赴昆侖誅殺刀宗。在這一部,燕寄羽邀請天下英雄華山論劍,乘鋒幫和正氣長鋒閣決戰在即,天下刀宗的種種隱秘終將揭曉。
秋蟬,鏽劍,青衫過雲影。
葉涼在桂樹下坐了一整天,書篋歪倒,滿地詩書狼藉,樹梢上隱約顫出燈芯的噼啪聲,是風刀剪落,霜花滿袖。
他翻遍了師父的藏書,仍沒能給那式劍法取出好名目。
蟬聲隨風東西,引得他思緒繚亂。七年前孤身流浪,初到臨江集這座小漁村時也是漫天蟬鳴,繞著他,追著他,勾動他腹中的饑鳴。那些蟬聲仿佛亙古已有,絲絲沁入岩土與草木,他口干舌燥,扯了一根草在嘴裡嚼著,幾乎疑心蟬鳴會在唇齒間迸開。
那日他在初夏的漁村裡徘徊良久,頭暈眼花,本想乞求一點喫食,卻隻討得些打罵;到黃昏轉至村後的野山,撞見山腰有兩間茅屋、一株桂樹,被稀疏的籬笆圍在半山餘暉裡。了,他看到一個中年男子坐在桂樹旁的石凳上,手捧書卷,面容和藹。
葉涼心裡一松,料想此人知書達理,必好相求。未及開口,那中年男子已站起來道:“小兄弟,你身上帶的可有飯食?我已經兩天沒喫飯了。”
葉涼一愣:“什麼?”
中年男子溫聲道:“你帶沒帶喫的?”
葉涼道:“沒有,我本來是想到山上摘幾個野果。”
“野果嗎?”中年男子搖頭一笑,“早被我喫光了。”
葉涼一時無言,腹中又咕咕響起。那中年男子笑道:“看來你也餓了,偏房裡有幾捆干柴,你背去江邊的陳家酒館,換些米回來。”
葉涼依了偏房,瞥見鍋灶邊的地上果然堆著柴,微一抬頭,雙目陡涼,卻是牆壁上掛了一柄無鞘的長劍,凜凜生寒。他不敢多看,背了柴徑自出門去了。
待葉涼換了米回來,中年男子問道:“可會淘米煮飯?”葉涼點了點頭,喜道:“那酒館的陳掌櫃多給了兩塊豆干哩。”中年男子一笑,指了指偏房:“有勞了。”
兩人坐在桂樹下各扒了三大碗飯。中年男子道:“你既換了米,何不一走了之,卻還回來?”
葉涼一怔,道:“我沒什麼地方可去。”
中年男子點點頭,似笑非笑地打量著葉涼,眉峰漸皺,忽問:“小兄弟,你幾歲了,父母安好?”
葉涼邊喫邊含糊道:“我今年十歲,父母都死了。”
“天無絕人之路。”中年男子道,“你既無處可去,不妨住下來,我這屋子雖陋能遮風擋雨;隻要每日柴勤些,便不愁衣食。”
說完見葉涼猶豫,中年男子又道:“你沒在半路上把豆干喫了,足見為人淳厚,如此我也不瞞你:其實我精通劍術,你若留下來拜我為師,我便傾囊相授。”
葉涼從前漂泊行乞,聽各地的說書人講過不少刀客劍俠的傳奇,早已心馳神往,當即答應下來。此後兩人便以師徒相稱。葉涼得知師父姓吳名重,已經“退隱江湖三年有餘”,不禁惋惜道:“江湖多好,師父為何要退隱?”
“若學多情尋往事,人間何處不傷神?”吳重搖頭長嘆,“不堪講,不忍提。”說罷徑屋去了。
翌日,葉涼起了個大早,叫醒師父,道:“師父,柴刀在哪兒?我去柴。”
“就在偏房牆上掛著,你昨日沒見嗎?”吳重翻了個身,又沉沉睡去。
從此葉涼成為臨江集個用劍柴的人。
數月後,葉涼從村民口中得知:三年前吳重路過臨江集時,看上了陳掌櫃的閨女,從此住下,隻是陳掌櫃嫌吳重窮困,不肯答允這門親事。而就在葉涼到臨江集前不久,吳重已花光了積蓄,三五天纔去一次柴,度日艱難。葉涼此時再回想師父那句“天無絕人之路”,似乎別有意味。
那天回到家,葉涼問吳重:“師父,你是愛慕村東的陳家姑娘,纔退隱江湖的嗎?”
吳重嗤笑道:“胡言亂語,為師是何等人物,哪般志向,豈會被一個村婦所累?”
晨光如柴,繁星似米,一趟趟地更換。山色依舊,劍刃卻漸漸生滿了鏽,葉涼一直也不知師父究竟算何等人物。
這一日,吳重去江邊酒館找陳掌櫃下棋,出門時交代葉涼給劍法取名。葉涼昏頭漲腦地翻了一天書,想著不知何時纔能翻過眼前這座山,去遠處瞧瞧。可是照師父的脾性,怕是要在山中終老了。
袖中山風,書頁飛卷如浪,葉涼心中靈機微皺,待風稍止,振劍將一瓣桂花挑過眉睫,霜意刺入眸中,他微微合眼靜候。冷香落上詩句,遮住“春風”二字。
“將就用吧。”葉涼拂開落花瞧去,嫌字眼有些尋常了。畢竟這是他僅會的一式劍法。
七年前,吳重言而有信,在葉涼拜師當日便教了他一式劍法。葉涼歡心雀躍,認真練了兩個時辰,對吳重道:“請師父教我第二式。”
吳重笑了笑,道:“再練練吧!”
葉涼見師父笑得高深莫測,不敢多問,整整又練了三天,纔去找吳重:“師父,請傳授我第二式吧!”
吳重哼了一聲,道:“貪多嚼不爛,先練熟式再說。”
葉涼迷惑起來,苦心琢磨這式劍術,反復請吳重講解,半月後道:“師父,我已經練熟了。”
吳重面色一沉,道:“學武練劍,忌,欲速則不達。你離真正練熟還遠得很。”
葉涼道:“那我練給師父看,哪裡練得不對,請師父指正。”當即施展了一遍。吳重皺眉看著,似乎也沒找出哪裡不對,道:“你再使一遍。”葉涼就又使了一遍。
吳重沉吟道:“嗯歸還是……還是不夠純熟。”
葉涼道:“師父,你是不是隻會這一招劍法呀?”
吳重一愣,隨即漲紅了臉,喝道:“,為師精研劍術,通曉的招式何止萬千?”緩了口氣,見葉涼似要追問,便又道,“你當前的練法,架勢是熟了,卻未得其神。手上有,心中無。”
一
一道道日光從刀鋒上折刺出去,浮動在草葉之間,宛如一團耀眼的雷電滾落在舂雪鎮上的一處偏僻院落中。——時值正午,楊仞手腕揮舞,腳下騰挪,認認真真地練完了當日的百遍刀法,忽而輕嘯一聲,收刀凝立。
春風掠過野草叢生的院子,楊仞擦去額上汗水,自知已將這路“乘鋒刀法”練得頗具火候,心中很是快意,算來自己已在這鎮上住了九年,到如今也滿二十歲了。回想九年前師父身染重病,臨終前帶著自己來到了舂雪鎮,說要將自己安頓在鎮上,當時自己還嫌棄這鎮子破敗,師父卻道:“刀宗雲荊山居於舂山峰頂,舂雪鎮便在刀宗腳下,可謂江湖中為之地,眼下你年紀尚幼,刀術未成,便到這鎮上久住,為師纔可放心。”
後來楊仞葬了師父,孤身入鎮,尋了一處宅院住下。宅院的主人名叫許念,是個七八十歲的老頭,為人古怪刻薄,神志也有些瘋癲素孤零零住著,很受鎮民們嫌厭。楊仞貪圖租銀便宜,對許念的性情倒也不計較,從此一老一少同喫同住。倏忽九年過去,此刻楊仞不禁心想:“師父當年所言不錯,我安安穩穩地在此地練了九年刀,果真也沒遇到什麼事端,本打算練滿十年再離鎮而去,隻可惜……”
正自轉念,忽聽有個沙啞蒼老的嗓音道:“楊小子,還在耍刀呢?”轉頭望去,卻見屋裡走出一個面容著粗布舊袍的老者,斜著一雙老眼賴裡賴氣地瞧過來,卻正是宅主許念。
楊仞聽出許念腔調有異,哈哈笑道:“許老頭,你當我耍把式賣藝呢?我這叫練刀,不叫耍刀。”說話中隨手振刀,刀聲颯然蕩開。
許念的滿頭白發在刀風中微微搖顫,不疾不徐道:“不得了,這便是昔年天下大幫‘乘鋒幫’獨門秘傳的刀術嗎?呵呵,我看卻也沒什麼厲害之處。”
楊仞九年來早聽膩了許念的嘲語,聞言隻微微一笑,卻不接話。他身屬武林中的乘鋒幫一脈,自幼追隨師父,常聽師父說起乘鋒幫在百餘年前聲威浩大,曾經稱雄武林,隻是後來日漸衰微,傳到自己這一代時已然人丁稀薄,但“自己的幫派曾是武林大幫”之事卻也深深刻在心中。九年前楊仞隨口對許念說起,許念卻嗤笑道:“老夫從前行走江湖也有好幾十年,可從沒聽說武林中有過什麼‘乘鋒幫’,多半是你師父杜撰出來騙你的。”
當時楊仞冷笑道:“你懂什麼,我乘鋒幫的獨‘乘鋒訣’、獨門刀法‘乘鋒十九式’,都是江湖中的武學,一旦修到高深境界,便能於天下。”
許念聽了自是不信。那時楊仞年方十一,本來越辯越是惱火,卻忽發奇想,對許念道:“如今我便是乘鋒幫的現任幫主,你若願意,我這就收你入幫如何?”
許念便問道:“不知貴幫派共有多少幫眾?”
楊仞道:“我也曾這般問過師父,師父說他本還有個師兄,但已失散多年,未必還在人世,當時師父嘆道,乘鋒幫多半隻有他與我兩人了……”話未說完,許念便已愕然失笑:“現下你師父也死了,貴幫豈非就隻剩下你小子了?哈哈哈,好一個天下大幫,好一個現任幫主……你小子還想收我入幫?真是個瘋癲小子。”
楊仞沒料到自己反會被一個瘋老頭說瘋癲,見許念不肯入幫,便也作罷。倒是許念九年將“天下大幫”當作“天下大笑話”提起,常常譏諷楊仞;楊仞倒也不太當回事,隻在無聊之際纔與許念鬥幾句嘴。有時許念閑坐院中看著楊仞練刀,往往胡亂評議指點一番,不是說楊仞的刀術破綻百出,便是挑楊仞呼吸吐納之法不對,楊仞自也懶得理會。
眼下許念見楊仞不接口,便又笑呵呵道:“敢問乘鋒幫現有幾名幫眾呀?”
楊仞一笑,道:“也沒有幾名,隻不過比你許老頭害死的人多一個而已。”
“胡說,胡說!”許念瞪眼道,“老夫一生作惡多端,害死的人比你小子見過的人都多。”
楊仞點頭道:“那我問你,你做過的的惡行是哪一樁?”
許念一愣,張了張嘴,卻似說不出話來,霎時露出迷惘神色,低頭沉思起來。
楊仞眼看拿住了許念的軟肋,便嘿嘿笑道:“許老頭,別想了,你想不起來的。”
九年前楊仞許念的宅院時,本以為這白發蒼蒼的瘋老頭隻是言行有些錯亂,然而沒住幾天,便發覺許念與尋常瘋漢頗有不同,每日嘴裡念念有詞,眼珠亂轉,嘴角掛著一絲獰笑,也不知都在盤算些什麼。某天,楊仞悄然許念,留神細聽,不由得心下駭異:原來這老頭每天咕噥的都是如何害死鎮上左鄰右舍的歹毒念頭。
許念察覺處的楊仞,衝他咧嘴一笑:“楊小子,我下一個便要害死你。”當時楊仞心中咯噔一下,問道:“咱倆無冤無仇,你為何要害我?”
許念微笑答道:“我與世人都無冤仇,幾十年來卻也害死了許多人。說起來我倒也沒什麼格外想害之人,隻是人生在世,不作惡又能做什麼呢?”
楊仞錯愕道:“好你個瘋老頭,竟以害人為樂。”
許念點了點頭,道:“你這話算說對了。”
楊仞好奇道:“那你倒來說說,你要如何害我。”
許念沉吟道:“若是在六十年前我年輕時,一掌便打斷了你的脖頸;若在四十年前,趕上老夫中年時,那便沒這麼便宜須折斷你的四肢,再給你喂下毒藥,讓你哀號三日纔死;若是二十年前,嘻嘻,那你可慘得很啦,我那時已攢下了百十種稀奇殘忍的法子……”
楊仞打斷道:“若是現下呢?”
許念神色古怪,壓低了聲音道:“你等著便是,不出五日我便害死你。”
楊仞將信將疑,小心提防了五六天,卻也不見許念來害自己,心想此人年老體衰,多半是怕我欺負他,纔故意說狠話嚇唬我;然而與許念相處日久,但見他每日念叨的不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覺地在全鎮井水裡下毒,便是要用糖果將鎮上孩童引誘到荒野中給豺狼咬死,這纔明白這老頭心思當真惡毒。當時便問道:“許老頭,你自稱行走江湖數十年,料想害死過不少武林中的成名高手吧?”
許念神情得意,道:“那是自然。”
楊仞道:“那你都害死過哪些武林高手,不妨說來聽聽。”
許念聞言一愣,支支吾吾,抓耳撓腮,半晌卻答不出一個人名,隻怪聲笑道:“我害死的高手可多了,嘿嘿,但我就是不說。”
楊仞心下雪亮,倘若這老頭當真害人甚多也該是武林中頗有名頭的惡徒,可自己從前從未聽師父說起過“許念”這號人物,多半隻是這老頭胡吹大氣罷了。當即又問道:“你一次害人,卻不知是害死了誰?”
許念冷然道:“我也不怕你知曉,半月前鎮上張獵戶的小兒子患病,我謊稱自己精通醫術,前去,趁機將他的小娃兒治死了。”
楊仞隨口道:“原來如此。”過得兩日,卻在鎮上聽聞:半月前許念確曾想去張獵戶家裡為其小兒子治病,卻連門都沒敲開便被張獵戶喝罵逐走了。楊仞回到宅院將此事說出,本以為許念要麼啞口無言,要麼惱羞成怒,哪知許念卻隻嘿嘿笑道:“不錯,我確是去張獵戶的家門,後來我便在門外一遍遍地祝禱神明,詛咒他的小兒子早早病死。你看怎麼著,那小娃娃還不是被我給咒死了。”
楊仞聽得皺眉,心說好在這老頭心惡手乏,沒有能耐真去作惡。往後九年,許念悶頭自語,喋喋不休,整日便是算計著如何害人。楊仞從不知一顆人心之中竟能積存下如此多的惡念,隻覺大開眼界。有時聽許念想出的陰謀毒計著實詭譎難防,有些甚至無須武力,便隻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也能施行。每當這時,楊仞便暗自留心,卻見許念隻是嘴上說說,從來也不去當真行惡,也就漸漸放下心來。
偶有一次,楊仞閑來無事,笑問許念:“說自己作惡多端,卻不知你所做過的惡行是什麼?”
不料一問之下,許念身軀一震,嘴唇哆嗦起來,似乎深受觸動,良久纔驚疑道:“問得好,你問得很好,隻是我忽然記不得了……”
楊仞冷笑道:“想來背地裡咒人便是你做過的的惡了。”
許念連連搖頭:“,我犯下的大惡,說出來駭破你的膽。”隨即徑自踱步凝思,不再理會楊仞,神情時而痴怔,時而焦躁,間或流露出一抹淒迷,口中忽而喃喃自語:“我明明做過一樁天大的惡,怎麼卻想不起來了……不成,不成,我須得好好想想……”
楊仞眼看許念一邊嘟囔,一邊在院子裡亂走,既覺古怪又覺好笑,從此倒也找到了一個竅門:每當許念聒噪糾纏,擾得他難以靜心練刀時,他便問一句許生所做惡事是什麼,許念便會徑自走去一邊,陷入苦思。
到今日正午,楊仞故技重施,果然再次奏效。許念歪頭晃腦,臉色焦急,良久過去,兀自苦苦追憶。
楊仞見狀嘆了口氣,上前拍了拍許念肩膀,道:“你這糟老頭子惡貫滿盈,惡行想之不盡,不如以後慢慢再想吧。”
許念頓時笑逐顏開,道:“不錯,我作惡太多,一時間哪能理清。”他心緒暢快起來,瞥見楊仞手中長刀,便贊道:“你刀術不濟,所用的刀倒是不賴。”
楊仞抬臂看刀,但見刀身清盈如水,幾乎要化散在陽光下,也不禁心中暗贊,哼了一聲,道:“這把寶刀名為‘清河’,乃是我乘鋒幫的掌門信物。”
許念頷首道:“這刀刃白晃晃的,像我的頭發。”
楊仞皺眉道:“這兩者豈能相提並論?”說著瞟了一眼許念的白發,心中忽生一念:自己初到舂雪鎮時,便見許念七八十歲樣子,如今九年過去,算來他也有八九十歲了,瞧著卻仍和九年前一般模樣,這卻有些奇了。隨即轉念:多半一個人老到一定歲數,樣貌便不會再變化,這老頭是當年便已老得不能再老了。如此一想,便覺豁然。
忽聽許念呵呵笑道:“楊幫主,該燒飯了吧?”
楊仞搖了搖頭,隨即也笑道:“許前輩,今日還是請你老人家燒飯為妥。”
他們兩人都不甚斯文素以“楊小子”“許老頭”稱呼對方,隻有到了燒飯的時辰,纔相互尊稱,推來讓去。楊仞並非嫌燒飯麻煩,隻是這許念雖然滿心惡念,廚藝卻頗為精妙,實在比他燒出的飯菜好喫十倍百倍。
卻見許念沉著臉道:“昨日便是我燒的飯,今該你了。”
楊仞恍若未聞,片刻後嘆道:“今日是我在鎮上的後一日,明日我就要走了,便有勞許前輩再燒一次飯,權當為我送行吧。”
許念怔了怔,默默轉身而去,燉好了一鍋野兔肉,又烹了一大碗山筍。兩了屋,對坐喫飯,許念忽然慢吞吞道:“住得好端端的,干啥子要走?”
楊仞心中微動,與許念對視一瞬,答道:“這兩日鎮上新到了許多武人,似都是衝著刀宗來的,隻怕鎮上要大變亂了。”
許念冷笑道:“原來你是怕了。”
楊仞哈哈一笑,道:“‘乘鋒刀法’天下,一對一老子誰也不怕,隻是好漢架不住人多,我又何必蹚這渾水。”
“原來如此,”許念陰陽怪氣道,“‘乘鋒刀法’天下,那你自然能勝過刀宗了?”
楊仞鄭重尋思了一陣,道:“嗯,眼下恐怕還勝不過,但等我尋到了刀譜,定然能勝過的。”
許念一愣:“什麼刀譜?”
楊仞道:“實不相瞞,我乘鋒幫世傳兩件寶物,其一便是這把清河刀,其二嘛,則是一本刀譜,上面記載著‘乘鋒十九式’的要旨,隻是太過玄邃難解,我師父當年領會得不深,我便也沒能真正學全‘乘鋒刀法’。”
許念道:“這倒從未聽你提過,不知那刀譜現在何處?”
楊仞道:“我師父當年和我師伯倉促失散,那刀譜落在我師伯手裡,他名叫梁炯,是冀州人,我此番離鎮,便是要到冀州去尋梁師伯。”
許念微笑道:“我記得你說過,你師伯多半已不在人世了。”
楊仞也不著惱,隻淡然道:“即便如此,梁師伯多半也已收下徒弟,將刀譜傳了下去,我能尋到他的弟子也是一樣。”
許念搖頭笑道:“江湖險惡,你梁師伯的弟子多半也不在人世了。”
“哈哈,隨你說去。”楊仞一邊低頭喫菜,一邊含糊說話,“告訴你,我便沒那刀譜,遲早也能勝過刀宗。”
許念慢條斯理道:“嗯,等你離了鎮子,我便天天求咒你,遲早能將你咒死。”
楊仞對許念的這類言語早就習以為常,點頭道:“好,且看咱們誰的命更硬吧。”
許念想了想,忽道:“眼下這鎮上亂哄哄的,你想安然離鎮,怕也不大容易吧?”
楊仞一凜,心說老瘋子此言倒不算糊塗,一時間沉吟不語。許念瞧出楊仞面色中似有一絲憂慮,不由得心中大樂,又道:“日沒出門,卻不知鎮上來的都是哪些門派的武人,可有勢力大過貴幫的?”
楊仞隨口道:“百年前本幫傲視武林之際,如今的停雲書院都還未出來,那也沒什麼好比較的。”
“停雲書院?”許念語聲恍惚,茫然回想片刻,道,“這是個門派嗎?依稀曾聽說過。”
楊仞聞言怔住,隨即心下暗笑:武林中誰人不知停雲書院,這老頭卻竟隻是“依稀聽過”,實在已孤陋寡聞到了極點。當即清咳一聲,正色道:“我來教教你吧,這停雲書院是六十年前柳空圖柳老前輩所創,到如今已是江湖中為鼎盛的門派……”
說到這裡,忽見許念目光顫動、神情恐懼,不禁奇道:“許老頭,你怎麼了?”
許念喃喃道:“柳空圖,這名字很耳熟……柳空圖是誰?”
一
一道道日光從刀鋒上折刺出去,浮動在草葉之間,宛如一團耀眼的雷電滾落在舂雪鎮上的一處偏僻院落中。——時值正午,楊仞手腕揮舞,腳下騰挪,認認真真地練完了當日的百遍刀法,忽而輕嘯一聲,收刀凝立。
春風掠過野草叢生的院子,楊仞擦去額上汗水,自知已將這路“乘鋒刀法”練得頗具火候,心中很是快意,算來自己已在這鎮上住了九年,到如今也滿二十歲了。回想九年前師父身染重病,臨終前帶著自己來到了舂雪鎮,說要將自己安頓在鎮上,當時自己還嫌棄這鎮子破敗,師父卻道:“刀宗雲荊山居於舂山峰頂,舂雪鎮便在刀宗腳下,可謂江湖中為之地,眼下你年紀尚幼,刀術未成,便到這鎮上久住,為師纔可放心。”
後來楊仞葬了師父,孤身入鎮,尋了一處宅院住下。宅院的主人名叫許念,是個七八十歲的老頭,為人古怪刻薄,神志也有些瘋癲素孤零零住著,很受鎮民們嫌厭。楊仞貪圖租銀便宜,對許念的性情倒也不計較,從此一老一少同喫同住。倏忽九年過去,此刻楊仞不禁心想:“師父當年所言不錯,我安安穩穩地在此地練了九年刀,果真也沒遇到什麼事端,本打算練滿十年再離鎮而去,隻可惜……”
正自轉念,忽聽有個沙啞蒼老的嗓音道:“楊小子,還在耍刀呢?”轉頭望去,卻見屋裡走出一個面容著粗布舊袍的老者,斜著一雙老眼賴裡賴氣地瞧過來,卻正是宅主許念。
楊仞聽出許念腔調有異,哈哈笑道:“許老頭,你當我耍把式賣藝呢?我這叫練刀,不叫耍刀。”說話中隨手振刀,刀聲颯然蕩開。
許念的滿頭白發在刀風中微微搖顫,不疾不徐道:“不得了,這便是昔年天下大幫‘乘鋒幫’獨門秘傳的刀術嗎?呵呵,我看卻也沒什麼厲害之處。”
楊仞九年來早聽膩了許念的嘲語,聞言隻微微一笑,卻不接話。他身屬武林中的乘鋒幫一脈,自幼追隨師父,常聽師父說起乘鋒幫在百餘年前聲威浩大,曾經稱雄武林,隻是後來日漸衰微,傳到自己這一代時已然人丁稀薄,但“自己的幫派曾是武林大幫”之事卻也深深刻在心中。九年前楊仞隨口對許念說起,許念卻嗤笑道:“老夫從前行走江湖也有好幾十年,可從沒聽說武林中有過什麼‘乘鋒幫’,多半是你師父杜撰出來騙你的。”
當時楊仞冷笑道:“你懂什麼,我乘鋒幫的獨‘乘鋒訣’、獨門刀法‘乘鋒十九式’,都是江湖中的武學,一旦修到高深境界,便能於天下。”
許念聽了自是不信。那時楊仞年方十一,本來越辯越是惱火,卻忽發奇想,對許念道:“如今我便是乘鋒幫的現任幫主,你若願意,我這就收你入幫如何?”
許念便問道:“不知貴幫派共有多少幫眾?”
楊仞道:“我也曾這般問過師父,師父說他本還有個師兄,但已失散多年,未必還在人世,當時師父嘆道,乘鋒幫多半隻有他與我兩人了……”話未說完,許念便已愕然失笑:“現下你師父也死了,貴幫豈非就隻剩下你小子了?哈哈哈,好一個天下大幫,好一個現任幫主……你小子還想收我入幫?真是個瘋癲小子。”
楊仞沒料到自己反會被一個瘋老頭說瘋癲,見許念不肯入幫,便也作罷。倒是許念九年將“天下大幫”當作“天下大笑話”提起,常常譏諷楊仞;楊仞倒也不太當回事,隻在無聊之際纔與許念鬥幾句嘴。有時許念閑坐院中看著楊仞練刀,往往胡亂評議指點一番,不是說楊仞的刀術破綻百出,便是挑楊仞呼吸吐納之法不對,楊仞自也懶得理會。
眼下許念見楊仞不接口,便又笑呵呵道:“敢問乘鋒幫現有幾名幫眾呀?”
楊仞一笑,道:“也沒有幾名,隻不過比你許老頭害死的人多一個而已。”
“胡說,胡說!”許念瞪眼道,“老夫一生作惡多端,害死的人比你小子見過的人都多。”
楊仞點頭道:“那我問你,你做過的的惡行是哪一樁?”
許念一愣,張了張嘴,卻似說不出話來,霎時露出迷惘神色,低頭沉思起來。
楊仞眼看拿住了許念的軟肋,便嘿嘿笑道:“許老頭,別想了,你想不起來的。”
九年前楊仞許念的宅院時,本以為這白發蒼蒼的瘋老頭隻是言行有些錯亂,然而沒住幾天,便發覺許念與尋常瘋漢頗有不同,每日嘴裡念念有詞,眼珠亂轉,嘴角掛著一絲獰笑,也不知都在盤算些什麼。某天,楊仞悄然許念,留神細聽,不由得心下駭異:原來這老頭每天咕噥的都是如何害死鎮上左鄰右舍的歹毒念頭。
許念察覺處的楊仞,衝他咧嘴一笑:“楊小子,我下一個便要害死你。”當時楊仞心中咯噔一下,問道:“咱倆無冤無仇,你為何要害我?”
許念微笑答道:“我與世人都無冤仇,幾十年來卻也害死了許多人。說起來我倒也沒什麼格外想害之人,隻是人生在世,不作惡又能做什麼呢?”
楊仞錯愕道:“好你個瘋老頭,竟以害人為樂。”
許念點了點頭,道:“你這話算說對了。”
楊仞好奇道:“那你倒來說說,你要如何害我。”
許念沉吟道:“若是在六十年前我年輕時,一掌便打斷了你的脖頸;若在四十年前,趕上老夫中年時,那便沒這麼便宜須折斷你的四肢,再給你喂下毒藥,讓你哀號三日纔死;若是二十年前,嘻嘻,那你可慘得很啦,我那時已攢下了百十種稀奇殘忍的法子……”
楊仞打斷道:“若是現下呢?”
許念神色古怪,壓低了聲音道:“你等著便是,不出五日我便害死你。”
楊仞將信將疑,小心提防了五六天,卻也不見許念來害自己,心想此人年老體衰,多半是怕我欺負他,纔故意說狠話嚇唬我;然而與許念相處日久,但見他每日念叨的不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覺地在全鎮井水裡下毒,便是要用糖果將鎮上孩童引誘到荒野中給豺狼咬死,這纔明白這老頭心思當真惡毒。當時便問道:“許老頭,你自稱行走江湖數十年,料想害死過不少武林中的成名高手吧?”
許念神情得意,道:“那是自然。”
楊仞道:“那你都害死過哪些武林高手,不妨說來聽聽。”
許念聞言一愣,支支吾吾,抓耳撓腮,半晌卻答不出一個人名,隻怪聲笑道:“我害死的高手可多了,嘿嘿,但我就是不說。”
楊仞心下雪亮,倘若這老頭當真害人甚多也該是武林中頗有名頭的惡徒,可自己從前從未聽師父說起過“許念”這號人物,多半隻是這老頭胡吹大氣罷了。當即又問道:“你一次害人,卻不知是害死了誰?”
許念冷然道:“我也不怕你知曉,半月前鎮上張獵戶的小兒子患病,我謊稱自己精通醫術,前去,趁機將他的小娃兒治死了。”
楊仞隨口道:“原來如此。”過得兩日,卻在鎮上聽聞:半月前許念確曾想去張獵戶家裡為其小兒子治病,卻連門都沒敲開便被張獵戶喝罵逐走了。楊仞回到宅院將此事說出,本以為許念要麼啞口無言,要麼惱羞成怒,哪知許念卻隻嘿嘿笑道:“不錯,我確是去張獵戶的家門,後來我便在門外一遍遍地祝禱神明,詛咒他的小兒子早早病死。你看怎麼著,那小娃娃還不是被我給咒死了。”
楊仞聽得皺眉,心說好在這老頭心惡手乏,沒有能耐真去作惡。往後九年,許念悶頭自語,喋喋不休,整日便是算計著如何害人。楊仞從不知一顆人心之中竟能積存下如此多的惡念,隻覺大開眼界。有時聽許念想出的陰謀毒計著實詭譎難防,有些甚至無須武力,便隻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也能施行。每當這時,楊仞便暗自留心,卻見許念隻是嘴上說說,從來也不去當真行惡,也就漸漸放下心來。
偶有一次,楊仞閑來無事,笑問許念:“說自己作惡多端,卻不知你所做過的惡行是什麼?”
不料一問之下,許念身軀一震,嘴唇哆嗦起來,似乎深受觸動,良久纔驚疑道:“問得好,你問得很好,隻是我忽然記不得了……”
楊仞冷笑道:“想來背地裡咒人便是你做過的的惡了。”
許念連連搖頭:“,我犯下的大惡,說出來駭破你的膽。”隨即徑自踱步凝思,不再理會楊仞,神情時而痴怔,時而焦躁,間或流露出一抹淒迷,口中忽而喃喃自語:“我明明做過一樁天大的惡,怎麼卻想不起來了……不成,不成,我須得好好想想……”
楊仞眼看許念一邊嘟囔,一邊在院子裡亂走,既覺古怪又覺好笑,從此倒也找到了一個竅門:每當許念聒噪糾纏,擾得他難以靜心練刀時,他便問一句許生所做惡事是什麼,許念便會徑自走去一邊,陷入苦思。
到今日正午,楊仞故技重施,果然再次奏效。許念歪頭晃腦,臉色焦急,良久過去,兀自苦苦追憶。
楊仞見狀嘆了口氣,上前拍了拍許念肩膀,道:“你這糟老頭子惡貫滿盈,惡行想之不盡,不如以後慢慢再想吧。”
許念頓時笑逐顏開,道:“不錯,我作惡太多,一時間哪能理清。”他心緒暢快起來,瞥見楊仞手中長刀,便贊道:“你刀術不濟,所用的刀倒是不賴。”
楊仞抬臂看刀,但見刀身清盈如水,幾乎要化散在陽光下,也不禁心中暗贊,哼了一聲,道:“這把寶刀名為‘清河’,乃是我乘鋒幫的掌門信物。”
許念頷首道:“這刀刃白晃晃的,像我的頭發。”
楊仞皺眉道:“這兩者豈能相提並論?”說著瞟了一眼許念的白發,心中忽生一念:自己初到舂雪鎮時,便見許念七八十歲樣子,如今九年過去,算來他也有八九十歲了,瞧著卻仍和九年前一般模樣,這卻有些奇了。隨即轉念:多半一個人老到一定歲數,樣貌便不會再變化,這老頭是當年便已老得不能再老了。如此一想,便覺豁然。
忽聽許念呵呵笑道:“楊幫主,該燒飯了吧?”
楊仞搖了搖頭,隨即也笑道:“許前輩,今日還是請你老人家燒飯為妥。”
他們兩人都不甚斯文素以“楊小子”“許老頭”稱呼對方,隻有到了燒飯的時辰,纔相互尊稱,推來讓去。楊仞並非嫌燒飯麻煩,隻是這許念雖然滿心惡念,廚藝卻頗為精妙,實在比他燒出的飯菜好喫十倍百倍。
卻見許念沉著臉道:“昨日便是我燒的飯,今該你了。”
楊仞恍若未聞,片刻後嘆道:“今日是我在鎮上的後一日,明日我就要走了,便有勞許前輩再燒一次飯,權當為我送行吧。”
許念怔了怔,默默轉身而去,燉好了一鍋野兔肉,又烹了一大碗山筍。兩了屋,對坐喫飯,許念忽然慢吞吞道:“住得好端端的,干啥子要走?”
楊仞心中微動,與許念對視一瞬,答道:“這兩日鎮上新到了許多武人,似都是衝著刀宗來的,隻怕鎮上要大變亂了。”
許念冷笑道:“原來你是怕了。”
楊仞哈哈一笑,道:“‘乘鋒刀法’天下,一對一老子誰也不怕,隻是好漢架不住人多,我又何必蹚這渾水。”
“原來如此,”許念陰陽怪氣道,“‘乘鋒刀法’天下,那你自然能勝過刀宗了?”
楊仞鄭重尋思了一陣,道:“嗯,眼下恐怕還勝不過,但等我尋到了刀譜,定然能勝過的。”
許念一愣:“什麼刀譜?”
楊仞道:“實不相瞞,我乘鋒幫世傳兩件寶物,其一便是這把清河刀,其二嘛,則是一本刀譜,上面記載著‘乘鋒十九式’的要旨,隻是太過玄邃難解,我師父當年領會得不深,我便也沒能真正學全‘乘鋒刀法’。”
許念道:“這倒從未聽你提過,不知那刀譜現在何處?”
楊仞道:“我師父當年和我師伯倉促失散,那刀譜落在我師伯手裡,他名叫梁炯,是冀州人,我此番離鎮,便是要到冀州去尋梁師伯。”
許念微笑道:“我記得你說過,你師伯多半已不在人世了。”
楊仞也不著惱,隻淡然道:“即便如此,梁師伯多半也已收下徒弟,將刀譜傳了下去,我能尋到他的弟子也是一樣。”
許念搖頭笑道:“江湖險惡,你梁師伯的弟子多半也不在人世了。”
“哈哈,隨你說去。”楊仞一邊低頭喫菜,一邊含糊說話,“告訴你,我便沒那刀譜,遲早也能勝過刀宗。”
許念慢條斯理道:“嗯,等你離了鎮子,我便天天求咒你,遲早能將你咒死。”
楊仞對許念的這類言語早就習以為常,點頭道:“好,且看咱們誰的命更硬吧。”
許念想了想,忽道:“眼下這鎮上亂哄哄的,你想安然離鎮,怕也不大容易吧?”
楊仞一凜,心說老瘋子此言倒不算糊塗,一時間沉吟不語。許念瞧出楊仞面色中似有一絲憂慮,不由得心中大樂,又道:“日沒出門,卻不知鎮上來的都是哪些門派的武人,可有勢力大過貴幫的?”
楊仞隨口道:“百年前本幫傲視武林之際,如今的停雲書院都還未出來,那也沒什麼好比較的。”
“停雲書院?”許念語聲恍惚,茫然回想片刻,道,“這是個門派嗎?依稀曾聽說過。”
楊仞聞言怔住,隨即心下暗笑:武林中誰人不知停雲書院,這老頭卻竟隻是“依稀聽過”,實在已孤陋寡聞到了極點。當即清咳一聲,正色道:“我來教教你吧,這停雲書院是六十年前柳空圖柳老前輩所創,到如今已是江湖中為鼎盛的門派……”
說到這裡,忽見許念目光顫動、神情恐懼,不禁奇道:“許老頭,你怎麼了?”
許念喃喃道:“柳空圖,這名字很耳熟……柳空圖是誰?”
雲 荊 山
舂山,夜半,雲閣。
堂中燈火搖曳,葉涼聽見身後傳來掩門聲,卻是燕寄羽走出門去了,葉涼手腕一顫,撤劍倒退數步,不自禁地跌坐在蒲團上。
在他面前,一個長發落拓的青衫人也下,眉目寧寂而舒朗。
葉涼低頭看看短劍,從劍尖上滴落一串血珠,再看那青衫人心口處的劍痕,卻無一絲鮮血溢出,心知是那人修為太高,雖被自己的劍勁摧毀了心脈,卻能控住體內血流,渾似無傷一般。
“雲前輩,你、你為何不還手?”葉涼顫聲發問,“你若肯出刀,恐怕我和燕山長……恐怕全江湖的武人都絕難傷你。”
青衫人端坐不語。
葉涼環顧空曠的堂中,一瞬間,一陣古舊清寥之感泛上心頭,仿佛燕寄羽並非方纔而是早已出門而去,徒留自己在此枯坐了數十年。
“雲前輩,我……”葉涼說到這裡,忽見青衫人面露微笑。
“小兄弟,我已出過刀了。十三年前,我便已出過一刀。”
“可那是十三年前呀,可是今夜、今夜——”葉涼聽得茫然,鼻尖一酸,哽住了喉嚨。
“我的刀,是無盡的。”青衫人灑然淡笑。
葉涼神魂一震,良久失語。心念翻飛不定,時而清明,時而悵惘:真有這樣的一刀嗎,從十三年前綿延至今?若有,這一刀此刻又在哪裡?
“小兄弟,你練刀多久了?”青衫人忽道。
“我隻練過劍,過柴,沒練過刀。”葉涼搖頭道。
“你的刀術不低,隻是尚不自知罷了。”青衫人深深看了葉涼一眼。
葉涼一怔,莫名遍體微涼。他凝望著青衫人的眼睛,倏然間滿心篤定,真有那樣的一刀,無限長久,無窮廣闊,與天地恆在。
而此刻,那一刀輕輕經過了自己,如夜風一般。
葉涼衣衫簌簌晃顫,神思空靈,起身長揖。
青衫人恍若未見,徑自問道:“那枚珠釵,現在何處?”
此問頗為突兀古怪,葉涼又是一怔,一幕幕光景從眼前掠過:
蘇州簡家,年輕的外姓弟子秦芸手中,一枚珠釵微微閃光;鄂州城中,吳重將珠釵交托給寧簡;青石鎮上,珠釵被簡青兮奪去,後又被江海餘取走,戴在了頭上;此後,弓魔孤身西行,直至舂雪鎮,終於與吳重見面。
一枚小小的珠釵,跨越萬裡山川和十幾年光陰,牽連了不知多少人的命運。
“我怎會記得這些,這其中有些事,分明是我未曾目睹過的……我、我此刻到底在哪裡,在做什麼?”葉涼惶惑起來,卻見青衫人眼神凝定而深邃,似看破了自己的心事。
“那枚珠釵現在江海餘前輩那裡。”——葉涼正要這般作答,驀地心弦一亂,眼前忽又浮現一些尚未來得及發生的事:弓魔面目漠然,被一眾停雲書生押送東返,掌中仍緊握著那枚珠釵;停雲書院後山,江海餘重又戴上珠釵,逃離了華山,一路跋山涉水,追著自己來到了臨江集;江岸邊,弓魔從珠釵中取出一根青絲,手指輕彈,發絲在自己眉宇間擦過,那枚珠釵卻掉落在地……
砰然一聲,恍如掉落在自己心頭。
——葉涼從夢中驚醒,隻覺衣衫潮濕,瞥見身畔野草上凝著一層露水,自己加入乘鋒幫後,隨眾人離開青州,風餐露宿,東行多日,算來已經入秋了。
蟬聲隱隱約約,他聽了一會兒,起身去尋楊仞,望見楊仞正在遠處與一名乘鋒幫刀客交談,走過去,卻聽楊仞叮囑道:“你到得靈州青簫白馬寨,務須親手將這封書信交與秦楚。”
那刀客領命縱馬而去;葉涼好奇道:“楊兄,你給秦……秦盟主傳信嗎?”
楊仞笑道:“不錯,咱日或要轉去靈州,便先送去拜帖。”頓了頓,又道:“聽聞秦楚與雷姑娘的婚期就日,葉兄,到那天我幫你搶了雷姑娘如何?”
葉涼臉頰微紅,隨即輕嘆道:“雷姑娘的心思,我從來也猜不透。”他不願多談此事,便說起江海餘的珠釵,楊仞沉吟道:“那日我去追殺燕寄羽,早早離了臨江集,倒不知弓魔死後,珠釵下落如何。不過葉兄為何提到這珠釵?”
葉涼道:“我夜裡夢見了一些去年舂山上的事,聽刀宗前輩話中意思,似乎這珠釵非同尋常,頗為重要。”
數丈外,方輕遊聽他言及刀宗,轉身走來,輕聲問道:“葉兄弟,當真是你殺了刀宗嗎?”
葉涼神情一黯,道:“我也記不確切,似乎……似乎是的。”
楊仞與方輕遊相顧一眼,未及說什麼,卻見賀風馗邁步;方輕遊不欲和賀風馗交談,徑自走離。
“幫主、葉兄弟,”賀風馗略一拱手,沉聲道,“那日在臨江集,賀某倒曾留意過那枚珠釵。當時大戰過後,葉兄弟去安葬那具焦枯的尸身,弓魔的尸體卻是由寧、陳主僕葬下……我瞧見寧姑娘撿起了地上的珠釵,本以為她會將珠釵與弓魔同葬,卻見她徑直將珠釵收入了袖中,還曾微覺詫異。”
“原來如此。”楊仞皺眉道,“真不知那珠釵有何不凡之處,下次見到寧姑娘和陳兄,可須得再好好瞧瞧。”
葉涼道:“那晚在舂山峰頂,雲前輩卻也未曾細說,他問完珠釵的事,便……”說著說著,倏而又覺遍體微涼,眼前恍惚暈眩,仿似又站在了雲閣之中——
青衫人閉目默坐,已然氣絕。
葉涼抱著青衫人的尸身,朝門外緩步走去,懷中的遺體輕得異常,渾如一片雲朵,仿佛一身氣血都隨著青衫人的逝去飄洩到了世界之外。
走到第七步時,葉涼醒過神來,隻覺天地寂靜,心中與心外都彌漫著哀傷。
段 峋
初秋,華山,木葉飄黃。
今日又輪到段峋為被囚的方天畫、鐵風葉等掌門送飯,他手拎食盒,心緒煩亂,走到後山時已快誤了午飯的時辰。
幾天前,燕寄羽歸返書院,段峋當日便從幾名師兄弟口中聽聞:臨江集一場激戰,不但柳老山長與方白殞命,副山長柳續更是為救護燕山長而死。
段峋震驚不已,郁郁失落,距九月十九的華山大會尚有兩個月,山上書生們卻已開始忙於修繕房屋,采買桌椅器具,人人辛勤籌備,似乎皆已將郭正慘死之事忘得干淨;段峋心不在焉,干起活來不甚賣力,已遭過師長一回訓斥。
“方前輩,晚輩送飯來了。”段峋敲了敲門了方天畫所居的陋室。方天畫正在床榻上酣睡,睜眼瞥了段峋一眼,呵地一笑。
段峋卻看也不看方天畫,將喫食擱在桌上,便告辭轉身,忽聽方天畫道:“兄弟,瞧你失魂落魄一般,莫不是山上出了變故?”
段峋悶聲道:“山上好端端,無甚變故。”說完便走向門口。方天畫又道:“柳續沒能為你師父報仇,是嗎?”
“你說什麼?”段峋一驚。
方天畫卻隻斜眼瞧著段峋。
段峋顫聲道:“你怎知道……怎知我請柳副山長幫我——”忽然住口,不再往下說。
方天畫道:“我不但知你請求柳續幫你報仇,還知你名叫段峋,是郭正的弟子。”說話中坐起身來。
“你、你……”段峋愈發驚疑。
方天畫道:“段兄弟,你不必慌亂,我隻是那日聽見了你在柳續屋裡與他的對話罷了。”
段峋不禁連連搖頭,他知方天畫被燕寄羽禁錮了修為,況且此屋與柳續所住的屋子還隔著三間房屋,無論如何也不信方天畫能聽得見。
方天畫淡然又道:“那日柳續憑一柄柴刀闖下山去,鬧得華山大亂,我本以為他就此與燕寄羽決裂,卻未想到他仍會舍身救護燕寄羽。”
段峋哼了一聲,道:“興許是柳副山長查明了燕山長的清白,先師遇害也並非燕山長所指使。”忽然神情震動,脫口道:“你、你一直被囚困於此,又如何得知柳副山長舍命之事?”
方天畫一笑,道:“那些看守在屋舍外圍的書生們這兩日可沒少議論此事。”
段峋將信將疑,暗忖:“難道此人的耳力當真如此靈敏……”卻聽方天畫又道:“如今戚晚詞雖死,燕寄羽卻仍活著,你若真想為郭正報仇,不妨便為方某做一件事,則燕山長死期不遠矣。”
段峋沉默片刻,道:“我是停雲弟子,如何能做危害燕山長的事?”
方天畫卻若未聞,繼續道:“你速速離山,尋到寧簡寧姑娘,為我傳一句話。”
段峋道:“方前輩,我絕不會幫你。”
方天畫道:“這句話隻八個字,便是‘明珠彈雀,時機已至’。”
段峋皺眉道:“……時機已至?”
方天畫嘆道:“不錯,算來距我在青州與諸多英俠結下‘青崖之盟’,七年了。當年我便勸柳續與我結盟,共抗燕寄羽,那時柳續與燕寄羽已頗為不合,卻仍不肯答應我,在我與鐵兄的圍攻之下重傷逃離……想來他心中自有執念,卻是至死固守。”
段峋暗自沉思那八個字的含義,一時卻不接口。
方天畫又躺倒在床,忽道:“或許確如段兄弟所言,燕寄羽和郭正之死無關,段兄弟還是莫要為我犯險,從此省心待在華山,他奶奶的安穩做你的停雲弟子,實為明智之舉。”
段峋眼瞧方天畫似笑非笑,也不知他此言是認真還是意存譏諷,隻道:“我自不會為你犯險。”言畢快步出門。
當夜亥時過後,段峋悄然出了寢舍,朝山下行去。
停雲書院門規森嚴,門徒不可隨意離山,段峋熟悉山上路徑,小心避開了夜裡巡山的弟子,繞過朝雲殿時,望見燕寄羽所居小院的屋裡燈火通明,頓時一驚。
燕寄羽素喜清靜,居處甚少有巡山弟子走動,故而段峋纔取道於此,卻不料燕寄羽深夜仍未歇睡,眼下若再院落,恐怕行跡洩露,不由得猶豫起來。
他本就對方天畫這等粗鄙放浪的江湖豪客很是厭惡,他的兄長段峻被天風峽刀客趙風奇所殺,而方天畫與天風峽掌門鐵風葉交好,那就更是厭上加厭,心說:“我是為了師父,絕非是幫方天畫。”當即屏息凝氣,緩挪腳步,仍打算從燕寄羽的居處旁經過。
走出十餘丈,驟聽側方有人語氣遲疑道:“……是段師弟?”
段峋大驚,轉頭瞧去,卻見一個年輕書生手捧一壇酒走來,段峋幾步,辨出他是齋舍執事盧修的弟子,名為張博日裡是掌管廚房膳食的,便道:“張師兄,你怎在此?”
那張博晃晃手中酒壇,笑道:“今夜有貴客遠道而來,正在屋裡與燕山長會談,我奉命取了這酒與貴客品嘗。”說著低頭酒壇嗅了嗅,咂嘴道:“據說這壇酒是柳老山長壯年時所留,可陳有數十年了,難得,難得。”
“那可真是稀世好酒了,”段峋應了一句,又道,“不知來了什麼了不得的貴客,大半夜的,擾動燕山長親自接見?”
張博隨口道:“我先前本在燕山長的屋裡伺候,卻也不認得那客人,那人是個模樣極老的老頭,說的是西域話,嘰裡咕嚕的,我也聽不懂,偶爾聽他提及柳老山長的名諱,語調很有些傷心,似乎對柳老山長的離世頗覺震驚。”
段峋點點頭,道:“原來如此。”
張博道:“但我今夜纔知,原來燕山長精擅西域話,與那客人對談如流,實在厲害。唉,燕山長他老人家當真是博學多能,無所不會。”
段峋道:“師兄所言極是。”心中卻閃過了郭正從前端正溫和的面孔。
張博道:“段師弟,你深夜經過此間,是受了哪位師伯師叔的召見?”
段峋一怔:“什、什麼?”
張博眨了眨眼,道:“你若不是受到召見,深夜不歸寢居,豈不違背門規了。”
段峋笑道:“是莊師伯召見我,我正要去見他老人家。”
張博打量他一眼,道:“那麼段師弟這便去吧,我須送酒去了。”
隨後,段峋繼續下山,一路東藏西繞,等遠離了山腳,已是凌晨丑時。
段峋回望一眼,華山隱沒在濃重夜色裡,他嘆了口氣,倏忽想起柳續離山前說的那句“此次我多半會死在外面吧”,咬牙加快了步伐,打算先在的村落尋一匹快馬。
便在這時,身後響起衣衫獵獵振動之聲,隨即眼前一花,一個灰衣方巾的中年男子已從他頭頂掠過,落足擋住他的去路,赫然卻是盧修。
段峋心頭凜駭,瞠目結舌,暗想:“看來張博終究將遇見我的事稟給了盧師叔……”他知盧修性情刻薄,處置起犯錯弟子手段狠,忍不住打了個寒戰,眼見盧修面目陰沉地盯著自己,片刻過去,卻一言不發。
段峋心念一動,覺出怪異來,心道:“盧師叔即便知我擅自離山,要追捕我,派些弟子便可,絕不該暗夜裡孤身一人前來纔是……”
隻聽盧修冷冰冰道:“憑你自己這點本事,也敢對燕山長搞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