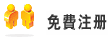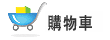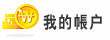第一章將知識和權力
帶入治療聯盟
卡特裡娜·布朗
重建同一性的敘事過程,需要超出對故事的簡單講述與重述,3而要對壓迫性的無益言論進行積極的解構。剖析無益故事、創造不同的更優故事,涉及對知識和權力之間關繫的認識,而知識和權力是通過言論交織到一起的(Foucault,1980a)。敘事療法的後現代敏感性取決於福柯對於權力和知識之不可分性的堅決主張,以及他為研究人們通過真理來管理和約束自己及他人的方式而付出的努力。因此,敘事,“不僅是意義的結構,也是權力的結構”(Bruner,1986,p.144)。對有關知識和權力的現代主義取向的反思,挑戰了從業者和來訪者可能在無意識中使壓迫性故事保持生命力的方式。
根據福柯對知識和權力之不可分性的理解,我采取了這樣的治療立場:知識並非總是好的,而權力也不等於約束。這種治療立場不再固觀念:一個人要麼有知識,要麼沒有;要麼有權力,要麼沒有。它瓦解了知識和權力的現代結構,認識到治療師和來訪者都是共建同一性這一治療過程中積極的表達性主體。
4我並不贊同傳統上所認為的治療師是專家、無所不知或一無所知的觀點,相反,我主張治療師和來訪者都是“部分的知曉者”。事實上,治療師和來訪者都會將知識和主使權帶進對話中。雖然我認為在治療聯盟中應該放棄“全知”治療師的觀念,縮小權力的區別,但我也覺得“一無所知”的立場對於挑戰壓迫性社會言論並無益處,且對於隨後解構消極同一性結論或重寫不同同一性故事也無一助益。
我贊同權力的新定義,它不再像現代主義一樣認為權力都是消極的、約束性的、壓制性的(Foucault, 1980a)。從這個立場出發,我認為,敘事療法承認存在著對主體生活的社會約束以及在這些約束之下的主使權和權力。除了說明福柯有關知識和權力的觀點對於解開來訪者故事中明顯的優勢社會言論和創作出更少壓制、更有助益的不同故事的重要性,我還將強調在重寫和經歷其生活的過程中認識到個體主使權和權力的重要性。
首先,我要談論的是敘事療法在解構優勢言論中的重要性,並在這個過程中挑戰了文化中經常影響人們故事的常態化了的真理。接著,我對這樣一個觀點提出了質疑:治療師和來訪者中,有一方是專家。我認為,治療師和來訪者都是部分的知曉者。接下來,我主張,如果治療師想要挑戰來訪者故事中內化了的壓迫性社會言論,並希望幫助創造不同的故事的話,那麼,他必須在對來訪者故事的解釋過程中采取一定態度或采取一定的立場。我探索了治療聯盟中知識和權力的限制性概念,並主張一種合作的治療關繫,在這種關繫中治療師和來訪者都被看做是積極的表達性主體,他們通過約束性(消極的)和建設性(積極的)的權力概念為治療對話提供了(部分的)知識和權力。本章強調,人們的敘事既受到社會的影響,也是他們自己主使權的創造物。這一觀點讓治療師看到人類不僅僅是社會的產物, 也是積極的主體。
解構優勢言論:聯結知識和權力
福柯(1980b)在他的著作中研究了真理和權力之新政治的可能性。對於敘事治療實踐和故事解構來說,最重要的是福柯(1980a)的觀點,
5即“權力和知識是在言論中結合在一起的”(p.100)。在《權力/知識》 (Power / Knowledge)中,福柯(1986b)主張:
權力的行使不可能離開特定的真理言論繫統,且這個繫統通過這種聯結並在這種聯結的基礎上運行。我們通過權力受制於真理的創造物,但如果沒有真理的創造物,我們也不能行使權力。(p.93)
福柯(1995)認為,“毋庸置疑,真理就是一種權力的形式”(p.45),因此,權力由知識構成(Tanesini, 1999, p.188)。在福柯的影響之下,懷特和愛普生(1990)同樣也提出,我們“總是同時參與到知識和權力的領域之中”(p.29),因此,治療實踐絕不可能都是良性的。懷特(1992)堅持認為,“知識的領域就是權力的領域,權力的領域也是知識的領域”(p.122)。同時,福柯和懷特還認為,知識和權力總是“相互交織在一起密切關聯”(Tanesini, 1999, p.195),不過,他們並不認為一個可以“化簡為另一個”(p.195),也不認為一切知識的論斷都是掩飾權力的手段。
但是,由於我們的生活經驗始終存在於權力和知識的領域或網絡內,所以,沒有哪個故事能夠處於權力之外 (White & Epston, 1990)。因此,任何對故事的聽與講述都不會是中立的(White, 1989)。 但是,在福柯 (1980a)看來,“哪裡有權力, 哪裡就有抵抗,不過,更精確地說,這種抵抗絕不會處在涉及權力的領域之外……在權力的網絡之中,抵抗無處不在”(p.95)。雖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做出沒有約束的選擇或“自由發揮” (Butler, 1993;Foucault, 1991),而是要為主使權和反言論留有空間。福柯(1980a)認為“言論不僅可以是權力的工具和影響,也可以是一個障礙、一個絆腳石、一個反抗點、一個反對策略的起點”(p.101)。因此,言論就像權力一樣,既可以將其視為建設性的,也可以將其視為約束性的。
後現代主義質疑我們是如何得知我們所知道的一切的;客觀的東西常常以故事形式呈現(Flax, 1990)。從後現代主義的視角看,知識是多重的,且僅僅隻是片面的。我們一般認為知識在社會性和歷史性方面是具體的,且不能獨立於權力的社會關繫。在後現代主義的觀點看來,有悖於真理的故事始終存在。布魯納(1991)認為,“知識永遠不會沒有立場” (p.3)。
後現代主義對敘事療法的影響明顯地表現在了這些觀點上:權力和知識是不可分的,人們通過真理的產品管理和約束自己和他人。6相反,現代主義在探索客觀知識時,則把知識和權力分離了開來。現代主義療法要求超越偏見、興趣和權力,通常主張要保持中立或客觀。我不贊同中立,相反,我認為有必要確定一個位置或立場。和懷特 (White, 1995, 2001;White & Epston, 1990)的思想一致, 我也認為,由於來訪者帶入治療的故事通常反映了優勢社會言論和權力關繫,因此,我們有必要解構和重建來訪者的故事,而不是讓故事保持完好無損(Brown, 2003)。因此,雖然現代主義者認為避免偏見可以更加客觀,但我認為,我們不可能不帶任何偏見,所以我們必須先承認自己的偏見,弄清並坦率承認自己所采取的立場。我們需要分析來訪者的故事是如何聯繫到一起的、占主導地位的觀念是什麼、故事中隱藏了什麼讓我們看不到的不同故事,而不是將興趣和/或權力隱藏在客觀性和科學的面具之下。敘事外化實踐將會改變這些無益的言論,使不同故事或更優故事的創作成為可能。
除了認識到在治療對話中治療師和來訪者之間存在權力差異外,重要的是不能把權力排除在所講述的故事,或者對故事的解釋之外(Flaskas & Humphreys, 1993)。如果治療師想挑戰壓抑,那麼,他們就必須先挑戰以優勢言論為基礎的故事。要想權力可以解釋,就不能將它從敘事療法取向中略去。在政治化的治療中,從業者必須搞清楚來訪者所講述故事的意思。站在社會正義一方的從業者對於權力不能采取中立的立場(Brown, 2003;White, 1994;White & Epston, 1990)。因此,從業者必須積極解構和重著壓迫性的故事,並進一步剖析這些故事中所體現的權力與權力關繫(Brown,2003;Fook, 2002;White, 2001;White & Epston, 1990)。這就意味著我們不能對這些故事采取中立的立場,而必須解開它們,以創作出較少壓迫性的故事。因此,我們將會從自己的敘事立場出發來解釋來訪者的故事。從這個意義上說,敘事療法包括精心整改壓迫性且通常占優勢的言論,以及解構其本身就是社會抵抗的反言論。不過,這並不是說我們隻是簡單抹去來訪者的故事,然後用敘事治療師重新建構的解釋來替代。
懷特將治療描述為一種政治過程,這個過程表明故事是在文化所認可的言論內在社會歷史背景中建構起來的。因此,敘事治療所感興趣的是故事建構,而不是固有的真理。來訪者的故事是多重的、變化的、不連續的——從本質上說不一定是實在的、真實的或不變的。在社會生活中,人們講述有關自己的故事,傾向於把這些故事當成真理。7不僅故事被當成真理,塑造故事的更大言論也被認為是真實的。這些故事被層層的社會建構真理所籠罩,它們本身被認為是絕對真實的。
來訪者常常將有關自己、同一性和生活的問題故事帶入治療中。這些故事常常包括內化的優勢社會故事,重要的是,故事本身往往是無益的。因此,當我們研究故事的真實效果時,關鍵點在於我們不能將故事當成“真實”。實際上,每一個有關故事主角自身及其經歷的故事,都涉及一些同一性結論。固化地認為故事是真實的、自我合理的,就會錯過打破有同一性結論的可能性。我們必須讓故事的層次性、復雜性和矛盾點都呈現出來。故事的多邊形、多重性、形態可變性都是探索不同理解、形成故事講述者所偏愛的故事的切入點。
外化故事的敘事過程第一步是解開和社會性地確定被述故事的起源和歷史。因此,故事不能脫離權力,而且需要完全地社會化。 這個過程可讓來訪者發現,故事本身並不是固定或絕對的,還存在其他的可能性。解構問題故事要著眼於重構更有效且更少傷害、病理化、責怪或壓制性的解釋。外化對話將會改變無益的言論,使我們能夠通過分析來訪者的故事是如何聯繫到一起的、占主導地位的觀念是什麼、故事中隱藏了什麼讓我們看不到的不同故事,從而創作出不同的或更優的故事。用懷特(2001年)的話說,重建同一性往往涉及“喚醒”以前沒有資格的或被邊緣化的聲音。外化內在問題故事的過程是反霸權的解構過程,它與之後重建同一性的過程都是治療中的政治性實踐。
全知、一無所知、部分知曉
在以合作為基礎的治療中,治療師常常采取一種“一無所知”的立場 (Anderson 1997;Malinen & Anderson, 2004)[1]。 這個觀點認為,來訪者是內容方面的專家,而治療師是過程方面的專家 (Anderson,1997)。安德森(1997)提出了如下觀點:
來訪者帶來了內容方面的專業知識:在他/她自己生活經歷以及促使他/她尋求治療的事物方面,來訪者自身就是專家。他們就是故事的敘述者,所以能夠體驗和8辨認出他們自己的聲音、權力和權威。治療師則在過程方面提供經驗:在讓來訪者加入以第一人稱講述故事的過程方面,治療師是專家。治療師和來訪者的角色似乎顛倒了。來訪者變成了老師。(p.95,原版中著重強調)
這種結構反映出人們想努力解決一個問題,即治療師在治療談話中擁有過多的知識和權力,同時認識到故事是對客觀現實的一種猜測。這條走出兩難境地的路線采取了一種一無所知的立場,它似乎能夠幫助克服治療師和來訪者之間權力失衡的問題,同時也避免了以客觀性為幌子提出錯誤的真理假說。 這一策略試圖將治療師的知識去中心化,強調以來訪者的知識和經驗為中心。安德森(1992)是這樣描述這種 “一無所知”的立場的:
治療師並不“知曉”先驗的東西(即任何行為的意圖),而必須依賴於來訪者所做的解釋。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通過學習和認真對待來訪者的故事,治療師和來訪者一起,共同探索來訪者的理解和經驗……“一無所知”並不是說會做出沒有事實依據或沒有經驗的判斷,而是說治療師要在治療會談當中建立更多的假設和意義。對治療師來說,興奮點在於研究每一個來訪者所敘述之真理(即他們充滿故事的生活中一貫的真理)的獨特之處。這意味著治療師總是會受到他們經驗的影響,但他們又必定會以這樣一種方式傾聽,即他們以前的經驗不能讓他們完全領會來訪者所描述之經歷的全部意思。隻有治療師站在一無所知的立場去了解每一種臨床經驗,這種情況纔有可能發生。不這樣做,就要尋找出可能證實治療師理論的規律和普遍含義,而推翻來訪者故事的獨特性,以及它們特有的同一性。(p.30, 原版中著重強調)
安德森是一位著名且有影響力的敘事治療從業者,他在工作中就采取了“一無所知”和“多重偏好”的立場。這促進了結構,認為來訪者是內容方面的專家,而治療從業者是過程方面的專家(Brown, 2003)。 結構試圖通過將來訪者置於“專家”的地位而最大化來訪者的權力,同時也含蓄地要求從業者讓出他們自己的知識和權力。例如,安德森(1997)就曾告誡說,我們絕不能讓自己參與到重寫或編輯來訪者的故事中,因為我們不是“精通一切的故事講述者”。
9將來訪者視為其生活的專家這種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會將“經驗”看做不可爭辯的真理。後現代女性主義者批判了這種觀念,因為它將經驗與其社會結構相分離了。當經驗與其社會結構相分離,就不僅僅是去情景化,還將經驗的焦點轉移到了個體身上。這種主觀主義的觀點通常認為經驗是中立的、個體的、與政治無關的(Alcoff, 1988;Fuss, 1989;Haug, 1992;Scott, 1992;Smith, 1990,1999)。相反,後現代女性主義認為,來訪者有關其經驗的故事通常都是社會性、政治性的。
當故事被理解為社會言論和社會關繫中的社會結構,它們的自我合理性就會更可疑,優勢故事就更有可能被解開。相反,主觀主義者對待來訪者故事的方法更可能不觸動優勢故事及壓迫性的故事。這至少有部分原因是他們沒有承認這些故事中知識和權力之間的關繫。通過采取一無所知的立場,許多治療師現在不再使用由傳統等級治療實踐發明的權力策略。奇怪的是,在這種一無所知的立場之下,來訪者的故事似乎逃開了讓知識和權力相分離的社會過程。人們認為這些故事以某種方式避開了權力的影響,它們被認為本來就是這個樣子,是自我合理化的。然而,來訪者的故事從本質上說和治療師的故事一樣,肯定不會脫離權力。這種治療觀念對知識和權力的構想導致個體成了焦點,而放松了對社會背景的關注,沒有努力揭示真實的、沒有修飾的自我,也沒有追求有助於解放的、承認並挑戰社會權力的社會實踐和認識論。
創作不同的或更優的故事:相對主義的局限性
在治療中援引“一無所知”的觀念意味著一種有潛在危險的相對主義,即在其中,所有的故事都被認為是平等的。如果一無所知成了避免采取一定立場、形成主張、發展分析或者對某人的知識和權力負責的方法,那麼,相對主義就顯而易見了。我建議,為了做好工作,我們需要采取一個立場:任何東西都不放過。有人認為,當為避免治療師控制治療而設計的以來訪者為主導的會談導致了“無目的的東拉西扯”(Malinen & Anderson,2004,p.68)時,可能就會導致道德和政治的相對主義。當在來訪者故事結構內權力仍然未被探索、保存完好且含糊不清時,10治療就會將優勢且通常無益的故事具體化。
我在這裡所采用的方法保留了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長處,摒棄了其短處。關於現代主義,我贊同它所提出的存在有助於解放的社會日程或遠見的可能性。有關後現代主義,我則贊同它所提出的知識始終是片面的、具體的,而絕不是中立的觀點。此外,後現代主義對解構的關注對於采取一種反身性的、不斷批判的分析是很有用的,特別是在剖析來訪者敘事的過程中。總的說來,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觀念的融合讓我們得以采取一定的立場,而不需要提出這種立場是客觀的。這樣,我們就能各盡其能,並知道自己的偏好所在。
我反對現代主義有關客觀的、價值中立的知識以及由此產生的總體的且通常本質化的真理假設。相反,我認為,所有知識都是由社會建構的。我也摒棄了後現代主義的相對主義傾向——無處不在又無處可尋的觀點——因為這不能讓人們擁有自己的立場,因而認為所有的立場或故事都似乎是平等的(Bordo, 1990)。“宣稱無處不平等卻又無處可尋”的相對主義立場(Haraway,1988, p.584)很明顯在治療中采用的是“一無所知”的治療師知識結構。盡管對於宣稱能夠“無處不在卻又假稱不存在”的絕對論來說,這種相對主義有時候可以說是一種進步,但科德(Code,1996, p.214)認為二者都不可取。波爾多(Bordo,1990)對後現代相對主義進行了描述:
它可能陷入了逃脫人類定位的幻想之中——通過猜想批評家能夠千變萬化,通過無止盡地改變看似無窮盡的優勢點;這些優勢點既不屬於批評家,也不屬於被評論文本的作者。(p.42)
制定這種千變萬化的幻想的解構主義讀物通過自相矛盾、反向、自我顛覆不斷地“滑離”……它們通常通過任何想要的方式展現自己。它們不用為它們的假設負責。 (p.44)
哈拉維(Haraway,1988)支持波爾多的觀點,他認為相對主義和客觀主義一樣,都是“鬼把戲”,是一種無處不在又無處可尋的觀點:
相對主義是一種無處可尋的方法,但它同時又宣稱它無處不在。這種地位的“平等”是對責任和批判性探究的一種否認。相對主義是完美的雙面鏡或者客觀意識形態的整體化;11兩者都否認定位點、具體化和片面觀點;兩者看起來都可能不錯。相對主義和整體化都是“鬼把戲”,都是無處不在又同樣徹底無處可尋的觀點。(p.584)
堅持社會正義反對壓迫和社會不公正的治療方法,不能勉強稱為相對主義,因為它們需要一個視角。因此,擁有立場意味著認識到所有的立場都是不等的。通過融合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方法,我們可以對社會變化采取一個立場和視角,而無需宣稱固守某一絕對的真理(Stanley & Wise,1990)[2]。 這種“兩者都”的立場允許個體做出真理斷言,同時承認真理始終是社會建構的,有定位且不完整。希望打破支撐和具體化社會權力關繫之優勢言論的療法不可能是相對主義的。
雖然我贊同在治療中不能過多給來訪者以指導,但權力之外的寫作似乎受到了誤導。決定了不直接指導或引導來訪者以後,安德森(1997)最終提出了一種關於治療中的知識的相對主義方法,他說:
我認為,這些修改來訪者故事的嘗試采取的是敘事編輯(narrative editing)的形式——修訂、校正或修改。治療師的任務不是去解構、再造或重著來訪者的故事,而是促進並參與到故事的講述或復述之中。
敘事編輯是一個急劇下滑。敘事編輯者需要專業的技術纔能夠編輯。這存在某種風險:它暗含了這樣一個假設,即治療師比來訪者更加精通人類故事。它假設治療師可以把來訪者當成一本書一樣去解讀。它讓治療師成了考古敘事者,他們相信存在一個具有想像意義的故事,需要去發現或復述。(p.96)
沃爾特和佩勒(Walter & Peller,1996)也強調,治療師既不能裁決來訪者的故事,也不能優待自己的敘事。同樣,帕裡和多恩(Parry & Doan,1994)認為,“每個人的故事都是自我合理化的”(p.26), 而“他人對故事正確性的質疑是不合理的。它們是壓制性的,從一定程度上說,主要是這些方法被用於壓制或降低人們故事的可信性,它們就是某種形式的恐怖主義”(p.27)。
另一種看法是,敘事療法涉及更有益故事的共著。這些新的故事也會被看做是社會化的非中立的建構,它們會隨時間而發生變化。采取一無所知立場的人常常會聲稱他們沒有任何立場:他們的偏見、12潛在的假設和基礎性假設仍然處於隱秘的狀態。正如不存在中立的故事講述或傾聽一樣,也絕對不存在中立的質疑。不存在任何中立的身體語言、聲調、面部表情、穿衣風格或裝扮。我們在工作中的定位、位置、角色、表現都不是中立的,問題不在於我們是不是中立。而在於我們是怎樣定位的,以及對此我們進行了怎樣的反思。
和懷特(1994)一樣,我認為,我們不能通過宣稱“一無所知”或者隻對有關過程的“專業”知識負責,而在治療工作中拒絕對我們的知識和權力所產生的影響負責。懷特(1997)倡導一種針對治療的平等主義方法,透明又可解釋——有利於解構有限的生活描述,挑戰權力的濫用,並避免產生權力的關繫。
與安德森的“一無所知”的立場相反,懷特(1989)強烈反對道德的相對主義:
個人的故事或自我敘說並不完全是我們腦海中虛構出來的。確切地說,有些東西是我們文化制度下不同的群體和人內部經過協商和揚棄而形成的……我們的生活是多層面的。任何一個生活故事都必定是含糊的、矛盾的。沒有任何一個個人故事或敘事能夠涵蓋所有生活中的意外事件……個人故事或自我敘事的影響絕不可能是中性的……不同的個人故事或自我敘事絕不可能有著同等的影響……敘事隱喻與一種傳統的思維習慣有關,即習慣性地排除了“什麼都可能出現”的道德相對主義的可能性……這種思維傳統鼓勵治療師為自己與求助者之間互動的實際效果或後果承擔責任。(pp.34)
當然,我們可以和來訪者協商知識和權力的範圍,來訪者和治療師雙方都參與對話,不害怕我們的知識和權力會讓自己因為試圖成為故事精通者而產生內疚感。我認為,通過回避的方式否認知識和權力的存在其實更加危險。富特和弗蘭克(Foote & Frank,1999)提醒我們應該特別注意那些聲稱自己處於權力之外的人。
知識與權力在治療聯盟中的定位
現代主義和後現代敘事療法對知識和權力的界定不一致。福柯對權力與知識的分析13表明,剖析社會建構的自我故事這個治療任務需要治療師和來訪者都成為積極的表達性主體,二者都要掌握知識、主使權和權力。後現代主義的治療聯盟觀認為,故事的講述、傾聽和重著中都有知識的參與。根據這一觀點,“知曉”有著多種共存的定位,這些定位通常是解釋性的、片面的。
人們通常認為,治療師在治療關繫中擁有更多制度上的權力,而來訪者通常更易受到傷害。通過強調來訪者的專業知識並最大化他們的權力來平衡這種關繫的做法,給治療師施加了某種約束:有必要否定他們自己的知識和權力。這裡隱含了一個假設:治療師手中所掌握的權力具有壓制性。在一心想提升來訪者的權力和主使權時認定治療師的權力從本質上說是有害的,這可能是有問題的,也是荒謬的。當人們“認為權力有悖於平等原則,隻能用於壓迫別人的時候”(Rondeau,2000,p.221),從業者自己便會恐懼,並會將他們自己的權力與壓迫他人混為一談。龍多(Rondeau)認為,從這個觀點來看,“所有的權力都不可信”(p.221)。
治療師們不再承認並技巧性地運用知識和權力,而是通過援引更讓人感到舒適的“一無所知”的姿態來試圖避開權力。不單這種姿態會冒被動性的險,連積極的問題解決或分析也用不著了。在第一種情況下,專家的知識和權力被否定了(即使很有經驗);在第二種情況下,治療師會因為害怕顯得太有知識或太有權力,而事實上落入沒有療效的境地。這兩種情況都是治療師因為害怕擁有“專業”知識或權力會對來訪者形成壓迫而做出的反應。安德森(1997)的觀點中明確地表達了這一點,他認為,編輯、修改或者重構來訪者的敘事是一個“急劇下滑”。總之,治療師的權力、知識和權威不是太“在場”,就是太“缺席”。
不過,福柯(1980a)認為:“權力從來沒有缺失過,它一直存在,並構成了人們試圖使用權力與之相抗爭的東西”(p.82)。權力存在於以消極壓制的權力觀、知識和權結構、知識和權力的分離、來訪者故事的自我合理化及專家化為基礎的治療聯盟的構想之中[3]。 權力存在於治療對話的講述與傾聽之中,也隱晦地存在於“一無所知”的姿態之中。一無所知並不是能解決權力的方法。
弗拉斯卡斯和漢弗萊(Flaskas & Humphreys,1993)觀察到,當一些具有合作精神的從業者關注治療聯盟中“權力的毒性”和壓制力時,很諷刺的是,14這些治療師會從人們的故事中審查權力。因此,盡管我們通過最小化治療師的專家地位來努力縮小治療師和來訪者之間的權力差距,但我們觀察到,“這與來訪者生活中有關權力的現實相去甚遠”(Flaskas & Humphreys,1993,p.38)。在論述對兒童期遭受過性虐待的個案的處理時,我們將對這一點做更進一步的闡釋,這種時候,采取中性的或一無所知的姿態可能會導致麻煩的後果。批評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不命名”權力比命名權力更為有害。
超越現代主權力結構
為了獲得更好的治療效果,治療師需要擁有知識和權力;問題在於怎樣運用它們。將權力建構為本質上是破壞性的,就反映出了一個被誤導了的觀念,即認為所有的權力都是消極的。現代主假設是,一個人要麼擁有知識和權力,要麼沒有,一無所知的姿態就體現出了這一點。因此,相應地,如果來訪者成為專家,他的權力就必定會變大,那麼,治療師就不能擁有知識,也必定會否認他或她自己的權力。
在治療中政治的地位是一個永恆的矛盾。我認為,無論治療師的政治取向和目標是什麼,我們都對來訪者的幸福負有道義上的責任。政治通常會在我們如何解釋故事、如何構建不同的故事、如何選擇治療對像等過程中顯現出來。盡管來訪者會在對話過程中被政治化,但從倫理上講我們的政治或世界觀不應該強加給來訪者。因此,我們必須做到在不強求來訪者的情況下堅守自己的立場。接受了個人的關繫結構就意味著承認(而不否認)治療師的知識和權力。在承認了他們的知識和權力後,治療師便更有可能為來訪者負責。而且,這一立場表明,在這些關繫中權力的範圍是可以商榷的。於是,治療師不用再為了提高來訪者的知識和權力而掩飾他或她自己的知識和權力;相反,二者的知識和權力都可以積極共存。
懷特和愛普生(1990)認為,福柯對於那些關於權力的觀點提出了另一種有價值的解釋,認為權力隻存在於語言之中,或者“權力真實存在,且被一些想要壓迫他人的人們行使著”(p.1)。現代主義的權力觀通常關注的是誰擁有權力、誰沒有權力,而不是也審視權力是如何運作的、權力的機制和策略是什麼(Foucault,1995)。福柯(1980a)的分析挑戰了看似毫無問題的信念,即相信在現代主義的權力建構中,“作為權力關繫之根基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始終且無所不包的對立面”(p.94)。15福柯認為(1986b):
一旦將權力的影響界定為壓迫,那他就采用了一種有關權力的純粹判決式的概念,將權力等同於“說不”的法律,當我們要強制執行某一禁令時,權力是首選。現在,我認為,這是一種完全消極、狹隘、簡化的權力概念,且奇怪的是,這個概念極為流行。如果權力隻是一味壓制,永遠隻說不,你覺得人們還會願意遵從嗎?權力之所以有效且被人接受,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即它不會隻通過說不來施壓於我們,還會提出不同的意見,產生一些東西,它會帶來快樂,形成知識,產生言論。我們需要將它視為生產性的網絡,貫穿於整個社會體繫之中,而不僅僅隻是一種具有壓制作用的消極存在。(p.119)
權力的積極面與消極面
在敘事治療中采納福柯有關權力的觀點讓我們超越了這樣的觀念,即一個人要麼擁有權力,要麼沒有權力。結果,這不僅讓我們把人們講述的故事理解為知識和權力的融合物,也讓敘事從業者將故事理解為社會約束和社會主使權[4]。 個體不再被極端化地認為是環境的絕對產物。在這種取向中,還存在一些機動的空間。畢竟,隻有當可替代事物有存在的空間,纔有可能創造出可替代的故事。拒絕將權力和同一性概括為一成不變或者靜態的事物,便可以制造出新的可能性和更多的新故事。在福柯看來,權力始終是相關的或交互式的,而不是整體的、單方面的或壓制性的。弗拉斯卡斯和漢弗萊曾說過,“抗拒,就像權力本身一樣,如果脫離了它賴以發生的關繫網絡,便不可能生存”(p.42)。他們認為:
權力是每一種社會關繫中所固有的一部分,所以它不能被分離出去。從福柯的立場來看,如果權力的影響受到挑戰,那麼,這種挑戰隻可能來源於權力關繫本身,這就是抗拒之可能性永遠存在的觀點,這為在壓制性權力關繫中發生改變帶來了一絲希望。(p.44)
此外,這種壓制性的權力觀認為,權力百害而無一利;生產性的權力不可能存在。福柯(1980a)以及隨後的懷特都認為,權力既是約束性的,又是構成性或生產性的。權力既有積極的可能性。也有消極的可能性。
16這一點明顯地表現在人們日常的交流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繫結構中,空間和構架的物理運用之中,對身體的真實訓練之中,以及在思想方式、主體性形式和知識形式的創作之中。因此,不管是起約束性作用還是生產性作用,權力始終存在。(Flaskas & Humphreys,1993,p.41)
權力,主使權和主觀性
福柯(1995)特別探討了這些問題:權力是怎樣產生的,怎樣運作的,它的策略或技巧是什麼,而並不關注是誰在行使權力。他的研究探索了人們是如何被變成我們文化中的主體,以及人們自己是如何讓自己成為我們文化中的主體的(Rabinow,1984)。在敘事療法中,來訪者的同一性故事證明了人們既受到社會的影響,同時他們又是其自身生活創造的積極參與者。
福柯(Fook,2002)重新闡釋了現代主義的權力觀,他反對這樣一個觀點,即“權力掌握在個別人手中,通常的原因是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那是‘擁有’權力,而不是‘行使’權力,因此更加穩固而不容易改變”(p.103)。福克害怕,這個有關權力的現代主義概念可能會變成“保持現存的權力不平衡狀態的工具”(p.103)。福克提出,我們必須考慮權力是如何行使的、它的真實影響,以及人們是如何“行使和創造他們自己權力的”(p.104)。她認為,“這包括理解人們可能如何參與他們自己沒有權力和有權力的生活”(p.104)。
有一種有關權力的觀點超越了認為權力是主觀的、有目的的建構,而承認權力是以一種更為隱蔽的方式行使的(Lukes, 1974;MacDonald & MacDonald, 1999)。權力關繫不受主觀意圖的簡單驅使,認識到這一點使得我們能夠在個體“違反自己的主觀興趣時——在沒有社會化和調節的情況下,做一些不希望別人做的事情——去揭示權力的微妙之處”(MacDonald & MacDonald, 1999, p.54)。這樣,個體即使不情願,也會經常參與他們無權力的活動(Fook,2002;MacDonald & MacDonald,1999)。從敘事的視角出發,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人們通過這種方式將優勢言論內化為他們自己的故事,此時,這些故事帶來的就不是更多權力,而是更少的權力(Brown, 2003;HareMustin, 1994;Sanders, 1998;White & Epston, 1990)。人們的故事常常反映了他們權力的缺乏,及其行使權力之能力的缺乏。這種“兩者都”的定位對敘事的重著過程而言非常重要,它包括徹底找到內化了的源於優勢社會言論的問題對話。
17懷特(1995,1997,2004)、懷特和愛普生(1990)描述了人們如何通過權力過程壓制其自身生活。敘事療法感興趣的是幫助人們對抗某種權力實踐,包括內化了的問題故事,這些故事會在他們的生活中慢慢累積。懷特(1995)認為,“內化了的對話模糊了經驗的政治,而外化的對話突出了經驗的政治”(p.24)。懷特對經驗政治的強調牢牢抓住了個體的主使權和權力。從這一視角看,問題是通過外化的過程得以解構的,這樣個體就可以遠離問題的影響,並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來生活。懷特舍棄了權力的回歸模型之後,通過強調經驗政治而采用了一種非本質化或非常態化的方式來外化經驗。懷特(1997,2001)很清楚,他的研究工作定位是反對權力濫用的,但他也堅持認為自己並沒有找到一種個人的或心理的解放性療法,可以讓人們通過擺脫社會壓制的束縛而發現真實的或真正的自我。這種心理解放的觀念不僅僅依賴於問題重重的自我本質論,也依賴於有限的權力壓制模式。
福柯(1980a)駁斥了有關權力的消極表達(一種建立在壓制基礎之上且要求服從的權力模式)。他提出:
這是一種隻有消極力量的權力,一種隻會說不的權力;絕對不會有所貢獻,隻能帶來局限性……這是對權力之效力的反駁:隻能指出哪些屬於主流事物,隻能做一些權力允許做的事情。(p.85)
雖然福柯駁斥這種消極的模式,但他同時也指出,這是一種為人們廣泛接受的觀點,因為它實際上掩飾或者說隱藏了權力運行的復雜性和隱蔽性。他認為:“權力隻有在隱匿了其大部分內容之時纔能被人們所容許。它的成功與其隱匿自身機制的能力是成正比的。”(p.86)權力當被視為一種壓制的時候,纔更能讓人容忍;而當我們自己被認為是壓制的積極參與者時,權力就不能讓人容忍了。
因此,福柯的權力觀改變了我們對經典模式的理解,在經典模式中,權力僅僅被認為是壓制的、消極的和約束性的。他的研究是對這種理解的巨大背離,因為它將我們的關注焦點集中到了人們是如何淪為權力之工具的,18這需要人們不顧其社會定位而時時刻刻都積極地參與。常態化的真理詳細說明了成為權力工具的個性形式(White & Epston, 1990)。懷特(2004)描述了這一過程:
是權力讓人們依據建構的文化規範,積極地參與塑造他們自己的生活、人際關繫,以及同一性——我們既是這種權力的結果,也是這種權力的工具。依據這種觀點,這是一個特別隱匿且普遍滲透的權力繫統。這是一種我們在自己的私密生活和關繫中隨處可以見到其具體運作的權力。(p.154)
當我們超越消極的權力觀,就可以認識到,人們既可以擁有權力,也可能受到權力的約束。從這一視角出發,外化人們的故事可以讓我們發現故事中受壓制的主流知識,認識到受壓制的知識和個體主使權對於重著不同的故事和重建同一性來說,是一個關鍵因素。當個體被構建為僅僅隻是受害者或產品,故事的其他方面就會變得模糊不清,且失去了資格。若人的主使權得到了強調,就更有可能出現對優勢言論的抵抗和違背。相反,當人們的故事去背景化了,他們社會權力的缺乏及其受到壓制的社會背景就會變得模糊不清。這樣,通過認識到權力既可以是約束性的,也可以是生產性的,通過在不把故事進行任何主體定位的情況下注意到人們故事中的無權與權力,我們便能夠對故事進行更為豐富的描述。懷特(1997)強調,即使是不同知識的產物和主體性也脫離不了權力,
盡管我們不一定會毫無知覺地參與到再造強加於我們生活的主體性過程之中……不同的生活模式和思維存在於話語領域——它們由知識、自我的技術、關繫實踐,以及文化的權力關繫構成。(p.232)
福柯的觀點對於敘事療法來說很重要,因為它不僅重申了自我創造是社會性的,也說明了社會性自我不能與知識和權力的過程相分離,同時也不能與消極權力和積極權力相分離。在主觀化的過程中,自我或主體的社會性構成需要人類積極主動參與,而不僅僅是被迫,這一點很明顯。人類創造作為主體的自我,部分是通過他們所講述的有關自我的故事。19這些故事憑借社會互動過程,起源於文化所允許的社會言論和權力的社會關繫。懷特(1995)提出,我們的故事不能反映或代表我們的生活;確切地說,我們的生活是通過我們的故事和敘事建構而成的(p.14)。此外,通過故事,個體將自己以及他們的生活融入到言論之中。不僅自我故事的建構依賴於自我的社會言論,自我實際上也通過個體所講述的有關自己及其生活的故事而融入到言論之中。因此,自我的產生不能脫離於言論、知識和權力的過程。
結論
通過引用福柯有關知識和權力之關繫的分析,我已經將敘事對話中知識和權力的現代主義構想問題化了。福柯對於知識和權力之不可分性的堅持,以及他通過真理的產物對人們管理自己及他人的方式的研究,是敘事療法的核心思想。外化、解構和重構優勢社會言論的核心是對知識和權力之間關繫的探索。我在本章中提出,希望在治療中避開權力和定位而采取“一無所知”策略的做法,通常會有具體化優勢言論的風險。和福柯一樣,我也反對權力的壓制模型,認為權力應該既是約束性的,也是生產性的。總的說來,我同意知識和權力不可分離的觀點,也贊同這樣一個觀點,即治療師和來訪者都貢獻了知識,並且都是治療對話中積極的構成動因。在我看來,如果我們希望避免非故意的優勢社會言論和社會關繫的具體化,我們就需要在概念實踐中有所反思。堅持政治化的實踐,需要治療師讓渡他們自己的知識和權力。
注釋
\\[1\\]盡管我對安德森(Harlene Anderson)“一無所知的定位”持批判態度,但我仍相信她為我們提供了有關自我、經驗和敘事隱喻的精彩討論(1997)。雖然她不認為自己是“敘事治療師”,但是她使用敘事隱喻,采用後現代的視角,並強調合作的方法。她所推行的“一無所知”的思想常常作為相對主義和本質主義的經驗被敘事治療師所采用。
\\[2\\] 雖然我在敘事實踐中分析知識和權力時采用的是後現代主義的視角,但我也堅持現代主義的信念,即可能存在一種支持社會公正的社會視角。因此,這種有關權力和知識的觀念是建立在混合的認知論或破碎的基礎論之上的。
\\[3\\]後現代主義對於權力的重新闡釋將會改變現代主義有關權力的構想,現代主義的權力觀認為來訪者的故事是專業的、自我合理化的。情緒和經驗這些傳統概念——即這些故事素,常態化和無爭議是它們的特征——受到了挑戰。情緒本身很少被解構或者被認為是一種社會建構物。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對多樣性和差別性的還原論取向。一些治療師似乎相信,如果他們承認自己的社會定位,就可以克服他們的偏見,從而獲得一種虛構的中立性。就像同一性、經驗的去常態化一樣,差異範疇也是如此。
\\[4\\]就像權力概念對於內在的消極同一性結論以及充滿問題之故事的外化來說非常重要一樣,對權力持一種反思的態度也很關鍵。權力在這些彼此相關的層面上非常明顯,不過並不局限於這些方面:(1)界定、內化問題的部分方式,以及決定問題由什麼構成的社會言論;(2)存在於社會建構和人們經驗的背景之中,包括社會定位;(3)存在於來訪者與治療師的互動中,盡管他們都努力地想使雙方關繫保持平等;(4)通過同一性的重建獲得更大的權力感和主使權感。在這些情況下,權力既可以被視為約束性的,也可以被看做是構成性的。例如,社會言論是具體化權力和構成現實的工具。然而,人們既受制於優勢言論,同時又抵抗優勢言論。在重建同一性的過程中,權力既可以被視為構成性的,也可以被視為生產性的;而這並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更優的同一性可能會受權力的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