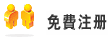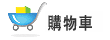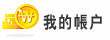| | | | 民謠(學者王堯長篇小說處女作重磅問世) | | 該商品所屬分類:圖書 -> 譯林出版社 | | 【市場價】 | 497-720元 | | 【優惠價】 | 311-450元 | | 【作者】 | 王堯 | | 【出版社】 | 譯林出版社 | | 【ISBN】 | 9787544785822 | | 【折扣說明】 | 一次購物滿999元台幣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2000元台幣95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3000元台幣92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4000元台幣88折+免運費+贈品
| | 【本期贈品】 | ①優質無紡布環保袋,做工棒!②品牌簽字筆 ③品牌手帕紙巾
|
|
| 版本 | 正版全新電子版PDF檔 | | 您已选择: | 正版全新 | 溫馨提示:如果有多種選項,請先選擇再點擊加入購物車。*. 電子圖書價格是0.69折,例如了得網價格是100元,電子書pdf的價格則是69元。
*. 購買電子書不支持貨到付款,購買時選擇atm或者超商、PayPal付款。付款後1-24小時內通過郵件傳輸給您。
*. 如果收到的電子書不滿意,可以聯絡我們退款。謝謝。 | | | |
| | 內容介紹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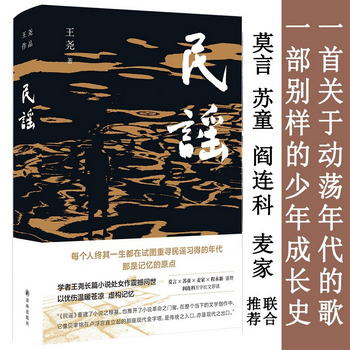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85822 版次:1 商品編碼:12829519 品牌:譯林(YILIN) 包裝:精裝 叢書名:王堯作品 開本:32開 出版時間:2021-03-01 用紙:輕型紙 頁數:344 字數:206000 正文語種:中文 作者:王堯
"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大眾讀者 1.學者王堯長篇小說處女作震撼問世
多位作家、評論家一致推薦:莫言親筆題寫書名,蘇童、麥家、程永新、王春林、程德培盛贊,閻連科萬字長文薦讀。王春林:《民謠》像金宇澄《繁花》一樣,是典型南方寫作的範本案例。程永新:到《民謠》,王堯已獲得一個真正有漢語之子的地位。張學昕:《民謠》屬於靜默於壺中的烏托邦,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是被煮沸的烏托邦。
2020年甫一發表,旋即入選多種年度榜單:2020收獲文學榜長篇小說榜、《揚子江文學評論》2020年度文學排行榜、探照燈書評人好書榜2020年度長篇小說。
評論界空前熱議,主流刊物《小說評論》《當代作家評論》《揚子江文學評論》推出評論專輯。
2.王堯是誰?二十年磨一劍,他從長江學者到“漢語之子”,引起文學圈驚嘆
王堯,作家,評論家。蘇州大大學文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曾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理論批評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等。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對長篇小說心懷敬意的學者王堯,一直在尋找自己經營的理想方式。二十年磨一劍,2020年,王堯推出長篇小說處女作《民謠》,引起文學圈震撼。“我可能因為這部小說成為小說家,不再是批評家了。現在寫小說就是小說家,寫散文就是散文家,寫詩就是詩人。我慶幸,我趕上了這麼容易命名的年代。”
3.《民謠》寫了什麼?一個少年的成長心靈史,一個村莊的變遷發展史,一個民族的自我更新史。每個人終其一生都在試圖重尋民謠習得的年代,那是記憶的原點。
王堯為他的長篇小說處女作《民謠》準備了二十餘年,他把自己的文學理想、文學追求、文學實踐都揉進了《民謠》裡,借此完成他重建個體與歷史之間聯繫的夙願。水鄉迢迢,且歌民謠。每個人終其一生都在試圖重尋民謠習得的年代,那是記憶的原點。
他以故事中人和故事看客的雙重身份,雜糅評點、抒情或批判,歲月流逝中的碎片和碎片不斷踫撞,顯露出新的縫隙,而小說由此拼湊出一條真正能夠進入歷史的現實路徑。
《民謠》融貫作者的創作理念:歷史是故事,人物是細節,以小人物的歷史詮釋歷史的破碎光影,以毛茸茸的細節探觸真實與虛構的邊界。以個體細微纖弱之小記憶,抵擋時代宏闊酷烈之大記憶,重返歷史瞬間。
“這二十年我自己變了,我想像中的人物、事件和筆下的人物、事件也變了,我*一沒有猶疑的是我總想在一個歷史時段的敘事中完成對自我的批判,並且在這個過程中呈現‘我’或‘我們’被歷史塑造的真相。”
4.《民謠》寫得怎樣?一個豐厚而異質濃體。《民謠》“重建了小說之根基,推開小說革命之門窗”。
2020年,在郁達夫文學獎的評審會議上,評論家王堯提出新“小說革命”的命題,引起文學界強烈反響,而《民謠》也可看作是作家王堯對新“小說革命”所做的文學實踐。《民謠》堪稱一個豐富而異質濃體:它用語言挽救語言,以記憶之纖維充盈文本,以個體記憶私化歷史。
閻連科認為:“《民謠》重建了小說之根基,也推開了小說革命之門窗,在整個當下的文學創作中,它像貝聿銘在盧浮宮直立起的那座現代金字塔,是傳統之入口,亦是現代之出口,而每一個從那入口、出口進出的人,愛與不愛大約都要在那駐足觀望一陣子。”
5.如何閱讀《民謠》?考究的作品紋理,豐滿的文本枝節,創造性的寫作框架,王堯以裡程碑式的文學實績,呼應龐大寫作野心。
一、文體結構上,全書分為四卷和雜篇、外篇,借鋻《莊子》內篇、雜篇、外篇的篇目結構,賦予文本更高的文學延展性和闡釋空間。
二、語言風格上,《民謠》既可看作典型的南方寫作的範本案例,紆徐宛轉中有盎然水意,又將語言肌理摸得透徹入骨,形成綿密雅致的豐厚文本。
三、敘述技巧上,少年到中年的多重視角切割,學生到知識分子的多種身份轉換,建構文本到解構文本的多維敘述嘗試,以具體而微的個人成長史角力宏闊酷烈的時代命運,重新探索自我與歷史的關繫,體現了小說以小搏大的磅礡野心。 內容簡介 “我坐在碼頭上,太陽像一張薄薄的紙墊在屁股下。”
時間撥回至一九七二年五月。依水而生的江南大隊,漫長的雨水終於停歇,麥子發酵味道籠蓋村莊,暗潮湧動於日常。碼頭邊,十四歲的少年等待著了解歷史問題的外公,江南大隊的人們等待著石油鑽井隊的大船,然而生活終以脫離人們預計和掌控的方式運行。少年在碼頭邊左顧右盼,在莊舍與鎮上間遊走返還,在交織纏繞的隊史、家族史、革命史間出入流連。他於奔跑中成長,於成長中回望,回望裡,記憶發酵,生長。歷史老樹的黃葉,一片片落入《民謠》的故事和人物,飄揚,旋轉,飛翔。
作者王堯為其長篇小說處女作《民謠》準備了二十餘年,藉此完成了他重建個體與歷史之間聯繫的夙願。他以故事中人與故事看客的雙重身份,雜糅評點、抒情批判,歲月流逝中的碎片和碎片不斷踫撞,顯露出新的縫隙,而小說由此拼湊出一條真正能夠進入歷史的現實路徑。這裡有故事,但波瀾不驚;它從歷史走來,也脫胎於每個日常;散曲民謠中包裹著唱不盡的人事變遷與世情冷暖。《民謠》鋪寫一個少年的成長精神史,一個村莊的變遷發展史,一個民族的文化與革命史。它以個體細微纖弱之小記憶,抵擋時代宏闊酷烈之大記憶。 作者簡介 王堯,作家,評論家。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曾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理論批評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等。出版學術著作多種,另有散文集《一個人的八十年代》、《紙上的知識分子》等,先後在《南方周末》《讀書》《收獲》《鐘山》等多家報刊開設散文專欄。 精彩書評 不同凡響的《民謠》歷時二十年,聚焦的卻是一個少年短短幾年的成長片段。在漫長的書寫過程中,故事的跌宕起伏早已化為歷史的煙雲,留下的隻是瑣碎的細節和無法復原的碎片。《民謠》說了太多的東西,同時又讓我們聽到了沒有說出的話;《民謠》之中有著太多的秘密,有些秘密在閱讀中會解密,有些秘密則永遠是秘密並吸引著我們。
——2020 收獲文學榜頒獎詞
《民謠》重建了小說之根基,也推開了小說革命之門窗,在整個當下的文學創作中,它像貝聿銘在盧浮宮直立起的那座現代金字塔,是傳統之入口,亦是現代之出口,而每一個從那入口、出口進出的人,愛與不愛大約都要在那駐足觀望一陣子。
——作家 閻連科
王堯的《民謠》,是一種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南方寫作,像金宇澄的《繁花》一樣,都是典型的南方寫作的範本案例。
——批評家、《小說評論》主編 王春林
到這一部小說,王堯已經獲得了一個真正有學位的漢語之子的地位。木心講,沒有審美力是絕癥,知識也彌補不了。一個有知識的人,又有審美力,所以《民謠》就出現了。
——作家、《收獲》主編 程永新
王堯的《民謠》屬於靜默於壺中的烏托邦,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是被煮沸的烏托邦。
——評論家 張學昕
這是王堯*次寫小說,一寫就寫長篇,還是這麼復雜的長篇,自我的操練和借鋻幾近空白,可謂難上加難。當然,小說創造史告訴我們,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
——評論家 程德培
整部作品,讀者就沉浸在“民謠”的緩緩調性中讀到了記憶,讀到了歷史,讀到了時代,讀到了故鄉、讀到了鄉愁、讀到了個人與歷史的關繫,讀到了過去與時代的連接。
——評論家、出版家 潘凱雄 精彩書摘 卷一
1
我坐在碼頭上,太陽像一張薄薄的紙墊在屁股下。
河水從西向東流過。大船,小船,木船,機船,偶爾也有竹筏蕩過。我愛聽搖櫓的聲音,像八哥兒鳴叫。機船高亢的聲音讓人心煩,但我喜歡機油的味道,在機船過後,我仍然能夠聞到殘留在河面上的油味。我說不清楚這種油味給我的感覺,機油和食油在水中會幻化成兩種圖景。隻有在寂靜的夜晚,你會聽到竹篙滑落的水聲像水珠落在荷葉上。如果是清晨,你坐在碼頭上,你會看到水的流向,無船駛過時,河水單純而自由。河水特別清澈時,你可以看到臨近岸邊的水草也在水中微微向東傾斜,小魚在水草之間遊弋。水面的寧靜不是魚兒的漣漪打破的,是最早有人到碼頭淘米的聲響。淘籮在水中晃動,蕩漾出夾帶塵埃的米水。這時,有魚兒過來了。你屏住呼吸,將淘籮輕輕沉入水下,魚兒進來了,吮吸著乳白色的米水。不急,再過幾秒,瞬間你將淘籮提出水面,三五條小魚兒在米上跳躍。米水在河裡散開時,如雲如絲。如果這一天我起早淘米了,我會把淘籮再沉入水中,讓小魚兒回到河裡。小魚兒吮吸著米水,像蠶兒剪裁桑葉。奶奶說,大頭,這叫放生。
五月,持續一個月的大雨衝垮了河水的單純與自由。從麥田淌到河裡的水染黃了河面,陰溝已經被大雨衝刷得干干淨淨。這條河,像陰溝了。現在臨近黃昏,我坐在第三塊石板上,河水已經退到碼頭的第六塊石板,第五塊石板見到太陽了。河水黃了,河面上開始漂著死魚。昨天下午,懷仁老頭兒撐著船,打撈浮起的死魚。他說,魚是死的,煮熟,人喫了,魚兒就是活的。老頭兒要我拿幾條回去,我沒有要,老頭兒說:“你是個獃子。”從四月到五月,小雨之後是大雨,大雨之後是暴雨,麥子在水中七零八落。太陽火了。這幾天開始退水了。渾濁的潮濕抑制住了麥子的霉味,陽光下,發酵出來的味道緩慢地擴散著。後來方小朵貼近我時,她覺得我身上還有這種味道。凡是空地都鋪滿麥秸,不必用腳踩,霉味肆無忌憚地衝出來,鑽進所有人的鼻孔,我們這個村子的人在一個季節都失去了正常的嗅覺。你若是把腳踩在麥秸上,霉氣就會在水泡中熱乎乎地張揚出來。
呼吸的不連貫讓我覺得這世界存在兩個空間,我一直處在飽和餓之間。你盯著路上的麥秸,眼睛會發花,霉氣嗆出了眼淚,時間久了,腦子像中毒一樣迷亂。想來,那些在空中飛翔的鳥兒也一樣聞到了霉味,它們逐漸從我的天空中消失,它們一定飛到了沒有霉味的遠方。如果在空中,像鳥兒一樣,我會怎樣?爬樹是升空的方式,但我不會爬樹。我瘦小,可就是不會手足並用,通常是抱著樹干,看同伴爬到了樹尖。我崇拜楊曉勇,他以前能爬到最高的樹頂上。我私下喊他勇子。勇子現在是大隊干部,不爬樹了。那時,看看在樹上的幾位同伴,我很尷尬,我的目光隻好盯著空中的麻雀,盯在偶爾飛來的喜鵲和在田野上空叫喚的烏鴉的羽毛上,它們是我那時見到的離開地面最高的動物。偶爾從村莊的天空中飛行而過的飛機,除了給我和同伴帶來騷動外,與我們並無關繫。我那時看飛機,如同看上海、北京,可望而不可即。我跟奶奶去鎮上,鎮上的天空沒有那麼多飛翔的鳥,那些家養的鴿子早就被訓練得不會自由飛翔,也幾乎看不到能夠撲撲翅膀的公雞母雞。我跟外公去玄字號那片農田,麻雀、喜鵲、烏鴉還有燕子,總是在天空盤桓,或者棲息在樹枝上,此起彼伏的鳥聲就像無數個嬸嬸、姨娘聚集在一起嘰嘰喳喳地說話。
這些鳥兒都飛走了,它們在新的棲息地歡叫飛翔。鳥兒是沒有故鄉的,天空都是它們的世界。我和它們不同。我看著船兒向東向西,或者靠近碼頭。在後來很長時間,一九七二年五月的大水,讓我覺得自己的脖子上掛著幾根麥穗。記憶就像被大水浸泡過的麥粒,先是發芽,隨即發霉。我脖子上的幾根麥穗,也在記憶中隨風而動,隨雨而垂。
外公的船也許快到西泊了,我屁股下那張紙好像也被風吹飛了。
2
從大碼頭上岸,是一大塊空地。老人說是村口,不老的人說是供銷社門口,現在好像都說是供銷社門口了。不錯,是村口,南河上的大橋就位於村口的中間。大隊檔案中存放的地契,標著這塊長方形土地的尺寸。我算算,差不多三百平方的樣子。你不能不驚嘆當年胡鶴義父親發家時對這個地方的規劃。現在我看到的供銷社,它的外部形狀像一個“凸”字,站在外面看,似乎是三幢房子的結構,進了門,中間是一個宏大的廳堂,兩側分別有三根像大人腰一樣粗的木柱子。從廳堂北門進去,是一個花園般的天井,兩側是東西廂房,走過小徑,就是胡家的堂屋,接待客人的地方。第三進是主人起居之所。等到我能夠在第一進房子走動時,廳堂的東側,成了百貨櫃臺,西側的櫃臺專門賣布匹。第二進是供銷社的倉庫,第三進是員工的宿舍。東廂房是廚房,西廂房堆放雜物。方小朵他們父女倆過來後,西廂房成了他們家的宿舍。
地主胡鶴義父親在門前留下這麼大的一塊空地,算是大手筆了。懷仁的這位老東家說:“留塊地方舞龍燈,唱唱戲。”外公年輕時候就在莊上舞龍燈的隊伍裡,獨膀子是敲鑼的人。等到胡鶴義從少東家變成東家時,他改變了老東家的奢華氣派。那個大堂,除了用於胡氏宗親的餐會外,他還辦起了私塾。李先生曾經是這裡的私塾先生。門前的空地,仍然舞龍燈,搭臺唱戲,但一年舞一次龍燈,戲臺子也搭不了幾次。這塊空地成了鄉村日常生活的舞臺,它敞開著,各色人等從這裡走過,停下,在這裡聚集,也在這裡散伙,從那時,一直到現在,隻是臺上表演的內容不同。我第一次表演,也是在這裡。
根叔一直說我第一次登臺是他扶我站在椅子上的。我記得根叔和疤眼一樣,最初也是拿著麻繩去綁人的,不知道什麼原因,他隻參加了一天活動。我一直回憶我在這個村莊的出場方式。我知道這很可笑,但在不斷的回憶中,我摸清了自己的來龍去脈。許多人糊塗一輩子,一個人今天的樣子其實與昨天有些關繫。根叔比劃著說:“你當時這麼高,芝麻稈一樣高。”他說話時的聲音悶在鼻子裡。芝麻稈參差不齊,我是高的那一根。根叔再次比劃時,我的個子已經高出天井裡的那棵桃樹了。桃樹是去年栽下的,好像沒有我長得快。奶奶說,這孩子瘋長了。
我差不多重復了父親當年站在這個碼頭上的疑問,這條河怎麼沒有名字?鎮上的河都有名字,鎮東的那條河叫牛河,鎮西的那條河叫小西溪。碼頭南面的這條河村上的人習慣稱它南河,莊北的那條河則叫北河。莊子的東西兩側分別是東泊和西泊。如果用線條表示,這個莊子是在南北兩條線、東西兩個圓圈之間。這個村莊的祖先,當年選了這個地方做莊。莊的東西南北,以天地玄黃命名了四片農田。農田裡聚聚散散的民居,我們叫舍。莊和舍拼在一起,就是村莊。我住在莊上,勇子、李先生、三小,他們住在舍上。我後來知道,革命烈士王二大隊長和勇子的祖父是舍上的鄰居。
南河西邊出了西泊有一條河,河向南再向西,可連通到鎮上。東泊與南河沒有銜接,南河向東穿過進勝大隊。進勝之前叫聖堂莊,一個非常奇怪的名字。父親說,聖堂莊上曾經有一座教堂,生我的那一年,大躍進中拆了。莊後的河也就是北河,西邊融通了西泊的北水面,東邊拐了個彎子向東北,流到吳堡大隊,拐向東南,便是東泊。大隊要在東泊圍湖造田了。平時大家說到的河,基本上是專指莊前的那條河,水碼頭也是專指莊前橋西的大碼頭。大碼頭向西,就是西碼頭,懷仁老頭兒就住在西碼頭的岸上。再向西,我們叫西曲口,外公的老屋就在西曲口上面。西曲口早就廢棄,當年遊擊隊王二大隊長常常在夜裡從西曲口上岸。王二大隊長在外公的老屋住過,母親說,他有駁殼槍。大橋北岸向東,還有一座小碼頭,我們叫它東碼頭。土改後,地主胡鶴義就住在通向大碼頭的巷子裡。莊上人有什麼大事,或者外地的船過來,都停靠在大碼頭,就是我現在坐的這個碼頭。
如果以供銷社為中軸線,供銷社東邊的巷子叫東巷,因為大隊部在這條巷子裡,大家又稱它大隊巷子。大隊部是一座南方式的四合院,從前,地主胡鶴義就住在這個院子裡,村莊的人叫它西院。穿過大門進去是天井。東廂房可能改造過,隻有南邊一個門樓,北邊一間房子,這間房子現在是大隊的油印室,進門時就聞到油墨味。坐北朝南的房子有三間,中間是會議室,東邊一間是辦公室,西邊一間是客房。公社、縣裡來人就住西邊的房間。南邊的一進,小間是儲藏室,大間是展廳。西廂房是電話間,值班的人也睡在這裡。我第一次跟小姨走進這個院子時,還有點膽怯。因為晚上要表演,小姨說要到大隊部去化妝一下。在會議室,
小姨指著東牆上的掛鐘說:“這是外公走了一夜的路,從縣城捧回來的。”那一年,我們的合作社是縣裡的先進。我沒有想到,過了幾年,我會在這間油印室忙碌,起早帶晚刻蠟紙,然後滾動油印的墨筒。大隊部對面的院子是胡鶴義家的東院,他的兩個兒子若魯和若愚從前住的地方,後來有一段時間成了我們村莊的小學。東院北面並排三進房子,南面並排兩進,一進是當年的糧庫,我在那裡讀到小學畢業。我們家住在供銷社西巷,再往西的巷子也一樣沒有名字。東巷熱鬧,不僅因為有大隊部和小學,還因為供銷社東牆張貼布告、通知,大字報也都貼在東牆上。那年我在大字報上看到了外公的名字,有人揭發他,還說到滿月後的我。我很慌張,爛貓屎都看出我的眼神不對了。 查看全部↓ 前言/序言 後記
我在這個年紀寫小說,有朋友形容是“老房子著火了”。其實,在“房子”不新不舊時,我便動筆寫了。
這幾乎是一次馬拉松式的寫作,與其說我在千錘百煉,毋寧說我一直處於寫作小說的困境中。過兩年寫幾段,再停下來,停頓的時間長了,我甚至忘記已經動筆的所謂小說。它成了我陌生的親人。有一天,我突然再起久違的寫作衝動,覺得應該下決心放下其他寫作,完成自己的那幢“爛尾樓”。親近的朋友早就熟悉我小說開頭的第一句話:我坐在碼頭上,太陽像一張薄薄的紙墊在屁股下。如果這句話是一塊鐵,那也鏽跡斑斑了。
庚子年來了,我體驗到了一種死而復生的感覺。和許多朋友一樣,這段時間的精神史可能是我們重新理解世界認識自己的一個重要環節。戴著口罩在住所附近漫步的那些天,我常常黃昏時分走到一座小碼頭,站在那裡什麼都想什麼都不想。一天,我突然發現水邊有一條紅花魚浮著,好奇地把它撈到碼頭上。這條魚開始紋絲不動,幾分鐘後魚唇吮吸了幾下,又死去了一般,我以為它是垂死掙扎。我把這條魚放回水裡,它和所有死魚一樣在水面上悲哀地浮著。就在我稍有悲憫之心時,魚兒突然一翻身迅速遊弋到小河的中央,然後沉入水中,無影無蹤。這似乎是另一種向死而生。許多東西就是這樣,你以為它死了,它卻活著,你以
為它活著,它卻死了,還有許多東西在半死不活的狀態。這個時候,我想起了我早就開了頭的小說。我能夠復活它嗎?復活昨天的文字,也許是為了今天的再生。魚兒在水中飛翔的那個瞬間,我似乎回到了莊前的那座碼頭。我把那條河稱為未名河,未名河的北岸,有一個少年在徘徊。
我無法想像我會在一座城市固守幾個月,就像我在那座村莊周而復始。去年底在南方一座城市參會,閑逛時聽到前面十字路口的東南側傳來二胡的聲音。青少年時期,我最親近的樂器就是二胡,我最早聽到的最好的音樂幾乎都是二胡拉出來的。許多人在十字路口等候紅綠燈,一撥行人走過後,我看到地上坐著一個和我年紀相仿的男人。他不是盲人,他的氣息讓我覺得他是我鄉親中的一位。我站在他的邊上,先聽他拉了《傳奇》。接著他拉了《茉莉花》,由《鮮花調》而來的《茉莉花》。我在他的旋律中想起我母親說她曾經在萬人大會上演唱茉莉花,她還說她那時扎著一根長辮子。在搖籃曲之外,我熟悉的民間小調和歌詞就是《茉莉花》、《撥根蘆柴花》和《夫妻觀燈》。曲子終了,這個男人起身,和我反向而行。我過了十字路口再回頭時,他已經消失在人群中。在熙熙攘攘嘈雜喧囂的市井聲中,《茉莉花》的旋律猶在耳畔。那個黃昏我從碼頭返回空空蕩蕩的路上,想起了十字街頭的情景。也許,我的這部所謂小說應該叫《民謠》。
終於安靜地坐下來,我在電腦上搜索斷篇殘章。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寫的一些片段中,自己筆下的那些人物長大了、衰老了、往生了,其中的一些人覺得自己不適合在我的世界裡生存而自動離開了。即便是我同輩繁衍的後代我幾乎不能完全辨識出他們的父親和祖父。我和筆下的人物相處太久,但彼此都有了熟悉的陌生。他們和我都變化了。但無論怎樣變化,我看到了少年的我在他們中間奔跑。故鄉是我寫作中的一粒種子,也是這粒種子最初的土壤。因為有他鄉纔有故鄉。但這個邊界其實是模糊的,模糊得我沒有鮮明的鄉愁,沒有鄉村與城市的分野,甚至也沒有追溯自己成長過程的欲望。
如果說我有什麼清晰的意識或者理念,那就是我想重建“我”與“歷史”的聯繫,這個重建幾乎是我中年以來在各種文體的寫作中不間斷的工作。我在文學批評、文學史研究和一段時間以來的散文寫作中,一直在詢問這個問題,我自己的清醒、困惑、迷失、尋找、反省、愧疚、欣慰等在這個過程中時隱時現。也許我並不是在尋找自己,我隻是詢問與我相關的一段或幾段歷史的那一部分。我個人隻是細節,歷史纔是故事。在我筆下的那座村莊,革命與現代化都是綿延不斷的存在。是烏托邦,也不是;是異托邦,也不是。世俗生活在這樣的是與不是中被切割,我的所有鄉親都在明白與糊塗中度過或即將度過他們的一生。如果我把這個村莊的故事和我們宏大的歷史相關聯,也可以勉強地說它有“整體性”。但無論是在生活還是在文本中,他們都是碎片化的存在。
這裡有故事,但波瀾不驚,故事中的每一個情節和細節我都有可能把它戲劇化,但我最終放棄了這樣的寫作。我想做的是,盡可能完整甚至是完美地呈現這些碎片和它的整體性。這樣一種安排情節和細節的方式,無疑給閱讀帶來了難處。我在當下的生活中,仍然感受到我追問的歷史以不同的形式呈現著,因此這些追問明顯地傳遞了我當下的某種思想狀態。
小說中的少年不是我,這部小說不是我的自敘傳。最初他身上有我的影子,後來他在成長中影響了我。我讀自己的初稿時,最初的感覺那個少年好像是我,再看又不是。我和他模糊了,我已經不知道是他影響了我,還是我影響了他。也許我從來沒有完全辨識過自己,這已經不是老生常談的哲學問題。這二十年我是在和他斷斷續續的對話中返回或離開那座村莊的。歷史的復雜性延續在他這樣後來成為知識分子的一類人中。我曾經設想,這個少年離開這個村莊後,會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心裡有很多答案,這些答案都讓我感慨萬千。但我知道,他是他們的一部分,但我覺得他和他們不同。他曾經坐在碼頭看船兒向東向西,曾經躺在田埂上看鳥兒自由飛翔。他比他們多了理想,也多了生存的能力。所以,我有意在小說的卷四和前三卷之間留下了一絲縫隙。我要留下年輕一代即使不能遠飛但心存飛翔的空間。
小說是世界之一種。我們在閱讀、訓練和寫作中認識了小說,並選擇了自己寫作小說的方式。盡管關於什麼是好小說也許有許多共識,但我們無法用一種小說定義另一種小說,正因為如此,在一種小說之外纔有另一種小說和出現另一種小說的可能性。在某種意義上說,小說的所謂創造性就是在小說定義和我們的閱讀經驗之外。我是一個毫無小說寫作經驗的人,但我的腦子裡充滿了關於小說的概念。這與我所謂“批評家”的身份有關,但我覺得沒有什麼“批評家”的“小說”,於是我寫作的過程是不斷放棄許多概念和閱讀經驗的過程。如果拙作與文學批評有關,那就是我自己對意義世界和小說藝術的理解影響了自己的文本,而不是突出了批評家的理念。我固執地認為,小說寫作需要思想、學養和多方面的文化積累。我們不是把思想、學養和文化積累附加在小說中,而是說思想、學養和文化積累影響了我們對世界的觀察和把握,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小說的故事、語言、結構和意義。換一種表述是,思想、學養和文化積累影響著我們對歷史、現實和人的理解。就此而言,批評家或學者寫作小說,如果他能夠在理念之外,找到自己的審美方式,他所有的資源將會提升他的寫作境界。
除了故事、細節、意像外,對語言和結構的摸索是我的重點。我曾經很長時間研究中國現代散文,也較長時間寫作散文,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寫作小說的語言。除了文學的淵源外,寫作者個人的心理、氣質和趣味影響了語言。這是大而化之的話。在苦思冥想寫了小說第一句話“我坐在碼頭上,太陽像一張薄薄的紙墊在屁股下”之後,我找到了小說的“調性”。“我”的敘述,是“我”的呼吸和心跳,這確定了小說的詞與物、人關繫以及語言的節奏;神經衰弱的“我”也讓語言在詩性之外多了一些迷幻;在完成《民謠》的過程中,我再次體會到隱喻是語言行為的結果。小說結構的問題一直困擾我,我想嘗試“形式”如何在《民謠》中成為“內容”,這就有了“雜篇”和“外篇”。我不知道這樣的形式是否推進了小說文體的創新,但它們都內在於小說的“大結構”之中。我設想“雜篇”不僅是補充了前四卷的細節,它還是“我”與“時代”的語言生活。在完成了“雜篇”之後,我意猶未盡,又以小說中楊老師的名義,寫作了他未完成的短篇小說《向著太陽》,用不同的語言敘述了小說中“圍湖造田”的故事,和卷三的故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用不無偏頗的話說,這麼多年來作為一種職業,我一直在認識小說,認識小說世界與外部世界的關繫。我覺得寫作者最大的困境之一是沒有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因而也缺少宏大的結構力。我寫過一些小說評論,但我覺得自己似乎從來沒有抵達過小說的深處。我沒有想過我會轉身對自己的寫作說三道四,這裡說的話應該不是《民謠》的副歌。我和我熟悉的小說家一樣,創作談的境界常常高於創作本身,但他們已經寫出了高境界的小說。我意識到了種種,但筆力不逮之處俯拾皆是。所以,我一直覺得創作談其實不是對自己文本的補充性闡釋,隻是在完成文本後發現了黑洞,想用微弱的光去照亮它;或者,在我是意識到了文本的問題,試圖用一些文本之外的議論表達自己雖然沒有寫好但還有幾句高明的話。我無法說《民謠》如何,但它的“異質性”是確定無疑的。
《民謠》的寫作可以說是敞開的。記得參與“華語傳媒大獎”評審的那幾年,我和永新兄經常通宵達旦討論小說,是離開既有理論和規範的那種討論。永新兄關於小說的理解完全超出了我的想像力,理解小說是需要想像力的。在和永新兄的多次暢談中,我在他身上理解了什麼是小說家的小說家。在今年閉門寫作的過程中,我不時有些遲疑和猶豫。我常常把寫好的章節、片段發小說家閻連科、批評家張學昕和我的同事季進、陳小民等,連科和學昕經常和我在電話中說出他們的具體意見。盡管我知道他們的評點我不會全盤接受,但我在意他們的看法。走走和朱婧熠首先讀到了完成稿,她們的肯定纔讓我鼓著勇氣弱弱地告訴永新兄和鐘紅明副主編我寫了部小說。在某種意義上說這部小說的“討論會”在寫作過程中已經“完成”了。莫言兄欣然為《民謠》題字,本書因此光澤許多。我向他們,也向所有關心我寫作的朋友致敬! 查看全部↓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