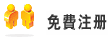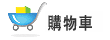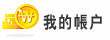| | | | 諾特博姆作品:狐狸在夜晚來臨 | | 該商品所屬分類:圖書 -> 譯林出版社 | | 【市場價】 | 608-880元 | | 【優惠價】 | 380-550元 | | 【作者】 | 塞斯·諾特博姆杜鼕 | | 【出版社】 | 譯林出版社 | | 【ISBN】 | 9787544785655 | | 【折扣說明】 | 一次購物滿999元台幣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2000元台幣95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3000元台幣92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4000元台幣88折+免運費+贈品
| | 【本期贈品】 | ①優質無紡布環保袋,做工棒!②品牌簽字筆 ③品牌手帕紙巾
|
|
| 版本 | 正版全新電子版PDF檔 | | 您已选择: | 正版全新 | 溫馨提示:如果有多種選項,請先選擇再點擊加入購物車。*. 電子圖書價格是0.69折,例如了得網價格是100元,電子書pdf的價格則是69元。
*. 購買電子書不支持貨到付款,購買時選擇atm或者超商、PayPal付款。付款後1-24小時內通過郵件傳輸給您。
*. 如果收到的電子書不滿意,可以聯絡我們退款。謝謝。 | | | |
| | 內容介紹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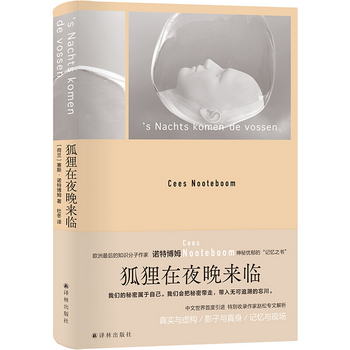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85655 版次:1 商品編碼:12959627 品牌:譯林(YILIN) 包裝:精裝 叢書名:諾特博姆作品 開本:32開 出版時間:2021-09-01 用紙:輕型紙 頁數:192 字數:100000 正文語種:中文 作者:塞斯·諾特博姆,杜鼕
" 編輯推薦 歐洲知識分子作家的典範、“作家中的作家”
“思想小說”,承繼納博科夫和卡爾維諾之後的文學傳統;
深受艾柯、庫切、A.S.拜阨特、艾斯特哈茲·彼得、雨果·克勞斯、托賓推崇
當代重要的在世作家之一,近年來屢次入列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名單。
神秘憂郁的“記憶之書”:八個故事共同的基調是“憂郁”,以通*者的超感追憶愛與故人,記寫存在與消逝、秘密與恐懼,沉思記憶的四個重要母題。
我們能附著於記憶多久?:對於愛人,我們有三次死亡的時刻——離開時,逝去時,被遺忘時。隻有當記憶都消散時,纔意味著真正的死亡。
重構記憶:回憶中,隱藏的心事得以坦誠,曾經留下痕跡的時空也重新拆解組合,生成一個關繫微妙且意味深長的多重戲劇的現場——這些失意者的經歷彼此反射與映照出人生的諸般樣貌,共同回應愛之創傷。隻有通過情感,人類纔能記憶。
照相與記憶,永恆的“缺席”:為什麼,以及如何啟動特定物品的情緒和記憶?那些看似尋常的老照片以異常突兀的方式揭示了記憶斷裂無序、殘缺的本質。
用記憶建造記憶:諾特博姆自如地把言語、意識、細節融為流動的整體,營造出微妙的空間。而超越這個精細建造的,是他構思故事的方式——用記憶建造記憶。場所、器物、光影、氣味、顏色,以及聲音都是他建造素,新舊交融,虛實共存,夢魘也是真身。
諾特博姆創作技藝終極之作,中文世界初次譯介,作家趙松專文解析
語境優美,哲思與隱喻精妙,融合小說、散文、遊記與藝術觀察等多種體裁。
漂浮,是現代人的宿命
漂浮在異國他鄉的人的命運:無依、無根,這是諾特博姆始終著迷的主題,亦是現代人共同的宿命。
精致的裝幀設計,優雅呈現“諾式斯文”
陸智昌裝幀設計,甄選日本進口內文紙和意大利進口封面紙。 內容簡介 夜晚,狐狸來臨,輕響,低語,微微喘息。
狐狸總在我們左右,恍如夢魘糾纏。
於是,我們徘徊在過去的人和事:誰會被銘記?又以何種方式被恆久懷戀?當這些從記憶中消散,是否意味著真正的死亡?
這八個故事主題相連,是對愛和記憶、生命和死亡的沉思。那些老照片所喚起的情感,那些逝去的愛人、錯失的自己、受了傷害的傻瓜,那些宿命的偶遇、無疾而終的戀情,讓我們收集和重建生活中那些悲傷的或失去的記憶。
人生隻在須臾,本來寂靜無聲。 作者簡介 塞斯·諾特博姆(Cees Nooteboom)
生於荷蘭海牙,當代重要作家,亦是詩人、旅行文學作家與藝術評論家。一生熱愛旅行,足跡遍及大半個世界,被譽為“*具有世界公民意識和風度的作家”。
他被視作卡爾維諾與納博科夫的同類,在文壇備受推崇,拜阨特稱其為“現代zui傑出的小說家之一”。代表作:《儀式》《萬靈節》《西班牙星光之路》《流浪者旅店》等。
自1950年代起,已出版五十餘部作品,至今仍筆耕不輟。曾獲飛馬文學獎、康斯坦丁·惠更斯文學獎、歐洲文學獎“亞裡斯提獎”,國際IMPAC都柏林文學獎,並因《邁向柏林之路》一書獲德國“聯邦十字勛章”。近年來屢次入列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名單。
杜鼕
南京人,摩羯座,十年文學譯者,七年記者與作者,藏地的旅遊開發者。在思維的漫遊中走上了許多條錯路,但依然希望以文字捕捉世界於萬一。譯有諾特博姆《流浪者旅店》《狐狸在夜晚來臨》,安東尼·伯吉斯《發條橙》,著有《康巴情書》《西藏的味道》。 精彩書評 現代zui傑出的小說家之一。他是一位偉大的歐洲作家。他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理解我們所經歷的歷史的表像,也因為他創造了新的虛構形式,在其中他可以記錄它們。
—— A.S.拜阨特
在這個文學如此專業化的時代,諾特博姆仍然穿著文人五彩繽紛的外套:詩人、小說家、旅行文學作家和翻譯家。他的作品本身就是藝術的像征。與納博科夫一樣,他的小說滿含暗示,哲思遍布在平常的敘述中。
——《紐約時報書評》 目錄 貢多拉
雷暴
海因茨
九月尾聲
最後的下午
寶拉Ⅰ
寶拉Ⅱ
海之角
後記 查看全部↓ 精彩書摘 《貢多拉》
貢多拉小舟令人思古。當他讀到這話時,他並不明白,即便現在他也不願意想,生怕會失去此刻的憂傷。太陽西垂,霧氣蒙蒙的潟湖上有一條黑色的貢多拉,如同飛鳥般的剪影,低矮的繫船柱如同孤獨的方陣大軍,在遠方逐漸隱去,仿佛受命要前去殺戮和摧毀,他則靜靜地站在斯基亞沃尼大道(Riva degli Schiavoni)之上,手中握著一張快照,已經發黃並撕去了一半——這的確夠得上悲愴吧?他們的貢多拉當時到港的地點大致就在這兒,他們走上岸的地方就在那兒,在臺階那,或者是更遠處的臺階,靠近一尊被殺害的女遊擊隊員的雕塑,半沒於水中。當時的天氣和今天相似,即便從快照上也看得出來。他們正坐在臺階上,就來了一位年輕的軍官,指著標志說這裡是水警專用碼頭。如今他隻需要找到那塊標志,想來不會太難。
可如果我找到了,又能如何?我就會和四十年前的自己站在同一個地方,那又如何呢?他聳聳肩,仿佛在回答別人的問題。本來就無可如何,他想,這纔是其意義所在。
為了進行這次奇特的朝聖之旅,他還同意了為葛拉西宮(Palazzo Grassi)的演出寫點東西。現在去哪裡?去尋找幻影,不,連這也談不上,去尋找一片空白。他很輕松就找到了那些臺階,如今依然是水警的泊地。古老之城都不會輕易改變,那塊標志依然在,釘在一側的磚牆上,不過最近剛剛重新漆過。他在最高的臺階上坐下來。當時那位年輕的國家憲兵隊(Carabinieri)軍官如今恐怕早已退休,可即便這四十年裡他青春不老,也未必能認出這位坐著的老者了。手中的快照是一位不知名的路人所拍,他背朝不遠處的潟湖,以三十度的角度拍攝,這樣就能把總督宮(Doge’s Palace)一同攝入畫面。湊近細看,他不由得贊嘆照片多麼會說謊。不但能召喚起死者,也能讓你和多年前的自己面面相覷。照片中的自己是一個長發的陌生人,如此有當年的味道,甚至能勾起早已消逝的前塵往事。
所擁有的依然是同一個身體——這真令人喫驚。可這絕對不是同一個身體。身體上附著的名字並未改變,這或許是唯一的共同點了。
他深思著,這張照片所真正承載的,與其說是憂傷或顧影自憐,倒不如說是一份聲明,是否就在那時,他開始思考隱退。他坐在她的左邊,她微笑著轉臉朝向那不知名的攝影師,從額前拂開紅發,彎腰抵著牆,將標記遮住一半。他看下去,灰暗的海水在低處的臺階上盤卷。一切依然是舊時情景,真令人喫驚!海水,如同鷺一般的貢多拉,他所坐的大理石臺階。隻有我們纔會退場,他想,我們將一生的種種風光拋在身後。他撫摸著身邊凹陷的石面,似乎在感受她留下的空白。他清楚,在此情此景下,心頭湧起的無非是老生常談,可這謎團卻永遠無解。現實和完美本是一回事——現在他懂得這話究竟從何而起了。很難說黑格爾所暗示的,是否是當下這樣的情景,隻是當下如此應景。一切都是偶然而生,絕無可能視其為理性,這想法莫名其妙地讓他如釋重負。死亡本是自然的禮物,卻時常會帶來如臨深淵的傷痛,你恨不得自己也墜入深淵,向死亡之謎的慘淡與真實投降認輸。
這一切的開始平淡無奇。希臘的小島,朋友的朋友的房子,借給他住是可憐他剛剛離婚,還沒有習慣獨居,渴望女人的陪伴。海岸邊有一條步道,閑逛的、漫步的女人都從這裡走過,他渴望上前搭訕,卻又不敢,擔心女人們笑話他,把他當作獃子。他的朋友溫特羅普過去總把搭訕女人叫作“Ankatzen”。這說法並沒有錯,可他卻總是做不好。魯塞伯特(Lucebert)的詩句是怎麼說的來著?長夜獨漫步,窈窕蘭舟過千帆。至少這一句很是真實。踱去踱回,踱去踱回,漫步,閑逛,觀望。許德拉的雕像,漁船,在沉黑的夜裡更加蒼白,港口中高大的鈉燈照耀下,輕輕隨浪搖擺。還有燕子、柏樹——但或許這都是他的想像?當時那裡就有了鈉燈嗎?不過,記憶又何必強求準確呢?就當那是黃色的電燈,聽到的是夜梟的啼叫,看到的是松樹的黑影好了。唯一不變的隻有輕拂碼頭的大海,其餘的一切都可改換,是裝飾你記憶的道具。
當她走來時,可一點都不像一條船,但或許也很相似:那必定是一條極輕巧的船,掛著孤帆,輕掠過海面。他當時看起來一定很滑稽,從碼頭上一躍而起,像警察命令停車一樣抬起胳膊。當時他就是這麼說的,停下!直到如今,他依然會對此覺得窘迫,當時的如此種種,待到一切已成往事後,他們還曾在加利福尼亞對此大開玩笑。她當時大喫一驚,停下了腳步。很奇妙,他不記得頭一夜她是否和他一同回家。他們在一家海港咖啡廳聊了許久。她是美國人,有一個意大利名字。是十六歲,或者是十八歲?他本想問,卻不敢問。他早早就注意到她的雙手和胳膊上的那些黑記,那是胎記,放在當今,倒更有可能是文身,烙在她曬黑的皮膚上。當他問起這些胎記時,她說,哦,我可是個女巫啊。這事在日後同樣讓他們為之大笑良久。他依然保存著當時她寫來的信,長篇大論地談著魔法和巫術,自鳴得意的長篇大論。他沒辦法把這些話當真,卻同樣為之著迷。她的愛好正合當年的潮流,可即便如此,也與她更為相稱:紅色的頭發,深灰藍色的眼睛,令人喫驚的低沉嗓音,甚至有些沙啞。後來的幾天,她睡在那座白色的大宅裡,卻沒有和他同床。這是兩人的協議,她隻允許他愛撫,以此來折磨他,卻不讓他摸臉,然後她沉沉睡去,帶著鮮明的、野獸一般的驕縱。他覺得自己有些傻氣,無關緊要,又為她的信任而感動。做伴比做愛好,他曾在日記裡這麼寫道。後來他把這本日記扔了,至今還為之遺憾,並依然能記得寫下這些詞句的場景。這樣的日子過了幾天之後,一切纔改變,或許這都是他的幻想。但他似乎還記得有一天她指著身上某一處奇怪的胎記說,今天是個做愛的吉利日子,因為行星排成了一行之類的,這類說法他當時就斥為無稽之談。
做愛時,她有些靦腆和孩子氣,他自然地想到了這兩個詞,卻知道其遠不恰當。靦腆絕不是準確的形容,她有目的,甚至有算計,但這些說法同樣不準確。她無邪的忸怩作態中有一絲觸犯禁忌的意味,讓他欲罷不能,似乎她在刺激他不敢與未成年的少女做愛。當時這對他是全新的體驗,日後也再無此事。
他轉身回城去,皮耶羅·德拉·弗朗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的展覽深深地影響了他。為什麼他會覺得這場展覽與幾十年前的一樁往事有相似之處呢?他也不知道,或許因為他同時沉浸於藝術家的作品和這段回憶中,又或許是因為其畫作中有些深意,無法明指,而與她共同度過的短短幾周也同樣如此。
不能說她是個神秘的女人,她掛在嘴邊的巫術也不過是孩子氣的胡話,可如今那個早已不在身邊的女人卻讓他想起藝術家畫中某些信仰者的形像。你站在畫前,渴望步入他們的世界,而那世界無門可入。為演出撰文之事已經讓他無從下筆,記憶中的一幕一幕也襲擊著他的情感。
那時他們曾乘坐火車橫穿整個希臘來到南斯拉夫,這段旅行在回憶中隻剩下片段:簡陋的客房和枕頭上如同光環一般火紅的長發。貝爾格萊德一夜,某家啤酒園,與一群酗酒狂徒共享梅子白蘭地,酒徒們還將喝干的玻璃杯舉起來砸碎在卵石路面上。然後他們就到了威尼斯。他忘記了當時住在哪家賓館,卻沒有忘記在哪裡拍了這張快照,他回來了,來尋找他記憶中的那些臺階。某些人就此從你生命中消失,這真讓人難以承受。 你非得有百倍的人生同時展開,纔說得過去。在火車站告別,走出車廂,回到聖盧西亞(Santa Lucia)車站,再次孤身一人,彙入人海,眼看自己被浩茫的世界再次吞沒,一隻纖細的胳膊伸出車窗揮手告別,一列火車隱入燈光映照出的鐵路橋的桁架輪廓之中,就此沉寂。四十年時光已過,他回到旅館,翻閱展會手冊。多麼荒唐啊,他還想在皮耶羅·德拉·弗朗西斯卡與這段經歷之間找出聯繫呢。
她是個怎樣的女孩呢?一個 1960 年代的“花童”女孩,而當時他孤身一人,迫不及待地想墜入愛河,渴望聽她大談行星與恆星如何影響人的命運,就好像星星們專愛插手人世間一樣!
可當深夜裡坐在水邊時,聽著她悠悠地說著水星和冥王星,似乎那是太空中的生命,紡起經緯的網,讓這個來自米爾谷(Mill Valley)的十七歲少女與來自阿姆斯特丹的自由藝術撰稿人穿越彼此。每當此時,他總會奇妙地被她捕獲,並不是因為她所說的種種,而是因為 她那藍灰色的眼睛如何在黑夜裡熠熠閃光。
愛是對愛的需求,至少這一點他還是懂的。將毫無生命的氣態星球和冰星球做種種分類研究,這是一個神話,人們隻不過絕望地想用這神話去取代其他已經褪色的神話,如果你沒法懂就一邊待著去,你這突然跳出來攔住別人的陌生人啊。
回到阿姆斯特丹空蕩蕩的寓所之後,他就等著她的來信,這個美國姑娘寫來的信字跡難看,甚至可算上稚嫩,信紙的邊角還點綴著生肖標志和西西裡符號,以抵擋邪惡之眼的窺視。他不記得自己究竟是怎麼回信的。他也不記得是誰沒有再回信,但清楚地記得那一天他多麼激動。二十多年過去後,他收到了一封信,還是那熟悉、潦草的字跡。她在舊金山舉辦的一場宗教藝術展的目錄中,讀到了他那篇關於雅克巴·馮·海姆斯凱克(Jacoba van Heemskerck)的文章。她說,她經歷了許多,結婚,離婚,有了兩個孩子,開始畫畫。她的有些畫作還會讓他想到雅克巴·馮·海姆斯凱克呢。她隨信附上了兩張照片,構圖是陰暗模糊的星雲,讓他想到她的眼睛,散射的高光點又讓畫面發灰。這是為禪修中心所畫的。她說生活不那麼如意,但佛教真的很有幫助。她常去附近的一座寺廟,要不是有孩子,她早就去那寺廟裡落發出家了。她會經常想起他,一定是心中的靈光閃動,纔會讓他寫到雅克巴的作品,此人在美國無人知曉,她卻將其視為靈感的源泉,更是生活中的慰藉。因為生活中總會倒霉,至於具體是哪些事,她就不和他細說了。她希望他能看到這封信,相信她自己會去看展覽本身就是個好兆頭。你曾經認識的人會消失得無影無蹤,這不奇怪嗎?你甚至不知道此人是否還活著,盡管你們曾一同旅行,分享過彼此的感受。她那時多麼年輕,不過是一個孩子,活在幻夢裡,還有許德拉的那座老屋,在干熱大地上那次漫長的火車旅行,最後抵達威尼斯,她希望有朝一日還能重訪。那時她的確說了許多昏話,老天啊,可他依然尊重她,她很感謝,因為這一切本可輕而易舉地就搞砸。她不知道他懂不懂她在說什麼,她是想說,他從沒有占過她的便宜。他不用擔心她有什麼目的,隻不過在數十億人中找到一個人本就是奇跡。當然,他也不是非回信不可,可她還是很希望能知道他過得如何。
如果要真實回答,他得說過得不怎麼樣。可他不會這樣如實回信,他也不會告訴她關於雅克巴·馮·海姆斯凱克的文章不過是另一個任務,他覺得此人的作品有價值,卻空洞乏味。就他自己而言,對雅克巴·馮·海姆斯凱克突然又產生了興趣,隻不過是由於人們對空靈純美(airy-fairyness)這種風格突然興趣大增,而此人是其中的領軍人物。此人的上色優美、動感甚至和康定斯基有相似之處,但他卻不喜歡。這一藝術風潮的興起,是對他非常討厭的十九世紀藝術的回應。這些他都沒有寫,他隻是告訴她自己在寫一篇關於皮耶羅·德拉·弗朗西斯卡的學術論文。她熟悉這位畫家嗎?是的,他很高興看到她的來信。如能再相見,真是物是人非啊!他還有她在斯基亞沃尼大道坐在繫纜柱上的快照呢。他給她寄過這張照片嗎?他不記得了。還有,小看十九世紀的全部藝術未免有失公平,真的,想想看,面對著撲滅了如此眾多希望和期待的麻木的舊世界,福樓拜、司湯達和巴爾扎克曾與之搏鬥。可他隻需要看看這些巨匠的銀版照片是如何相似,長時間的曝光讓他們何等僵硬,就會知道自己多麼討厭被困在現代主義的前廳,即十九世紀。那張快照!女孩坐在碩大的、足以讓遠洋輪繫泊的短柱上。薄薄的衣服,略帶紫色,再向上就是青春易老的面容,如同沙塵一般無常。她就像一幅貝利尼所畫的聖母像,這話他從沒有對她說過,一位藝術史學家在比較時必須謹慎。其實,即便沒有懷抱嬰兒,她已經是聖母了。左臉上同樣投射了命定悲慘的陰影,陷下的眼窩,已經成百次預見孩子躺在她膝上死去這一慘劇必將發生,還有那孩子,一位瘦長的哲人,也已知道當死亡來臨時,母親親切的雙手將無法保護他。
還沒有看完她的信,他就決定了,他要去見她,於是他就去了。無的放矢,有位朋友如此評價這次旅行,但他卻不這麼想。這段往事尚未結束,那便讓它結束吧。
結束往事包括前往美國之旅,有個女人在舊金山機場處迎接,她的面容告訴他,他自己如今也已年華老去。人生多美妙,應當一次又一次地巧加裝點。如今是見面瞬間就有所察覺,在心中留下一張快照,清晰至極,無可比擬。她的眼邊已經有了紋路,依舊是火紅的頭發,卻微微泛出灰色,時間的印跡突然讓他覺得親切,甚至溫柔。比起往日,他湧起更多的愛意,這他立即就知道了,但他並無心於此,這他也知道。這情感比往日更加脆弱。她住在一座遠郊的木屋內,畫著魯道夫·斯坦納(Rudolf Steiner)風格的水彩畫,這風格他從來就不喜歡,要是在以前他會直接指出來,如今卻發現避而不談更是輕而易舉。你依然是個夢想家,他說。她依舊是當年的她,聲稱是土星讓她開始了水粉畫。她說自己整整有一周都在狂喜中,整夜整夜地沐浴著這能量,當一切都結束後,她覺得自己比以往更加空白,雖空白,卻欣喜。
那之後不久,她就去看了展覽,並獲得了啟示告訴她給他寫信。可她絕沒有想到,他會親自來美國。
他當時所想的詞是“事後安慰”,他是來結束這段往事的。
結束與完結並不相同,依然有著可能性。事情一般總是這樣:有一段情緣,然後分隔兩地,時間流逝,疲倦與淚水,然後是遺忘。時而會想起,拾起模糊的回憶,這是常理,一切總是這樣過去,除非你決定采取行動。其中依然缺了些什麼,缺了互道告別的過場。事情總要收尾,這不僅僅是為了你,也是為了對方,除非他們根本不在乎。所以他來到了米爾谷。如今她已經故去,所以他來到了這裡,威尼斯。
她不是在信中提到過那些艱難時光嗎?她生活中的不幸?是的,但她現在不想談。
她建議一起去海邊散步。天氣不錯,風不小,但還算宜人。他是不是太累了?不,他很想走一走,想感受海風拂臉。不過遊泳就免了,海水太冷,更別提還有迅猛的海浪;海邊景色很美,卻很兇險。
的確如此,馬林縣(Marin County),麥克魯白海灘(McClure’s Beach),沿著漫長的下山路,兩邊都是草地,大群壯實的麋鹿奔馳其間,這是保護物種。正是發情季節,麋鹿巨大的鹿角相互撞擊時發出的吼聲不絕於耳。再向下走,就是呼嘯的海浪,翻卷起一道道波牆,磯鷂趕在海浪前匆匆行走於沙灘之上,留下微小的爪印。高亢的風笛聲久久不去,二十年前開始的故事,在此地結束正是應景。正如向風中發喊。
宿命與終結,這樣的想法與美國大陸的色調並不合拍,這裡大人都穿著孩子般鮮艷的衣服,牆板也粉嫩艷麗,人智學高峰期時荷蘭女畫家的畫作也有人模仿。於是你向大海走去,將自己的言語拋向海風。海浪聲中一個女人在訴說,悲嘆詩人從她身邊逃走,一個孩子染上了毒癮,身染隨時會發作的惡疾,但我已經學會了接受。
的確承受了太多,你不覺得嗎?她後來在車裡說。正是這句話陪著他一路來到了威尼斯:承受了太多。他們後來又通了幾次信,但當問及她的健康時,她都不回答。行星與恆星如今和我更加親近,她如此寫道。她已經感到,她會被星星托入天空。她要送給他一幅自己的水彩畫,等她的日子到了,就會送到他手上。他並不為她傷心,她已經從海邊走回,日落得正好,如帶的落霞漫過沙灘,正好落在她腳邊,讓她在海浪上行走,一直向天邊走去。
幾周後,他收到了那幅水彩畫,她曾將這畫掛在牆上,他則不會。他還收到了最後幾個月裡自己發出的信,還有二十年前自己寫的舊信,他沒有讀,都丟入了潟湖中。該丟垃圾桶裡的,身後有人說。他沒有回答,隻是看著信紙在灰暗的、如夜色般的水面上散逸,漂遠,一條貢多拉駛過之後,再無蹤跡。 查看全部↓ 前言/序言 《漂浮的世界裡生命轟然倒地時的模樣》
趙松
塞斯·諾特博姆
年輕時,他很瘦,有著典型荷蘭人的窄臉龐,頭發柔軟彎曲,眉毛濃黑,鼻子堅挺呈45度角。這是一張他年輕時的黑白照片。當時他正側歪著頭,握著筆,懸停在留白寬闊的打印樣章上方,西服是深色的,雪白的襯衫,扎了條有很多小菱形圖案的領帶,也可能是淺黃色的,或是淡金色的。從為數不多中年以後的照片上可以看出,這張臉已變得松弛舒展起來。沒變的,是他喜歡側歪著頭,眉毛略微上揚,眼神淡定而又有距離感地看人的樣子。他這個人不管神情如何淡然,似乎都有種骨子裡透出的得體且不失寬容的驕傲氣息,與此相應的,則是意味深長的眼神。隻有在跟好友們,比如雨果·克勞斯,或是翁貝托·艾柯在一起時,他纔會露出親切默契的笑容。
我對諾特博姆的有限印像,其實是被雨果·克勞斯喚起的。2020年8月裡,讀完那部厚厚的《比利時的哀愁》,我又讀了諾特博姆跟隨雨果·克勞斯返鄉完成的那場對話。這對老友在那座比利時小城裡漫遊,追溯過往記憶,解讀小說與現實的關繫,也展現了彼此在文學上的共鳴與交情的深度。在跟隨他們的腳步和眼光遊蕩的過程中,我也在回想與諾特博姆相關的記憶。自1956年出版第一部詩集後,這位1933年出生於荷蘭海牙的作家,至今仍寫作不輟。我不知道他到底寫了多少作品,但早就讀過已翻成中文的兩部小說(《萬靈節》《儀式》)和三本遊記(《流浪者旅店》《西班牙星光之路》《通往柏林之路》)。這次讀了《狐狸在夜晚來臨》之後,我好像又一次重新認識了這位荷蘭當代文學大家。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在諾特博姆的漫長人生中,應該是把很多時間花在了到處漫遊上。這不隻是因為他寫了那些遊記體傑作,在讀《狐狸在夜晚來臨》的過程中,我發現裡面的主要人物多數都是生活在異國他鄉的荷蘭人,而且,他在寫這些人物的時候,無論以何種方式呈現他們的命運,都會賦予他們隻有在異國生活的情況下纔會有的某種氣質,尤其是在看他以簡練而又富於詩意的筆觸去描寫那些異國風物時,你甚至能感覺得到,它們的存在,不僅讓那些荷蘭人沉湎於漂浮異鄉的生活狀態,還始終都強烈地吸引著他的熱情與步履。
我沒讀過他的詩,但我絲毫不會懷疑他是位優秀的詩人。在讀《狐狸在夜晚來臨》的過程中,我就知道,能以這樣變化微妙而又層次豐富的方式寫小說的人,要說他不擅長寫詩,幾乎不可能。幾乎每篇小說裡都可以隨便挑出一些片段,分行就是好詩。但,這還是表面的。往深了說,就是他有本事能讓小說的行文過程中不時透露出令人著迷的微妙詩意。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漂浮的生活與靈魂
那麼,《狐狸在夜晚來臨》究竟是一部什麼樣的作品呢?
它由七篇小說組成,因為《寶拉Ⅰ》和《寶拉Ⅱ》其實是一篇,但我不會把它看成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短篇小說集,而更願意把它視為一部小說。下面,我要先為這些小說做一下簡要概述,然後再闡釋為什麼它們最終生成的是一部小說作品。
一個老男人,來到威尼斯,回憶多年以前在此結識的少女,他們燃起短暫的激情,然後各奔東西。後來她結婚生子,離婚學畫,然後偶然看到他的藝術評論,發現他評論的那位畫家正是自己最喜歡的。他去美國看望她,為了結束。後來她死了。他的追憶充滿哀傷與絕望。(《貢多拉》)
一個木刻藝術家,害怕鼕天,害怕陰冷的氣候,因為黑膽質性格。他喜歡風暴天氣。在海邊,他和戀人目睹了一幕意外的慘劇:一個喜歡拍閃電的女人跟討厭她做這事的男友發生爭執,然後他端著酒杯走向海邊,被閃電擊斃。藝術家在回家途中,鋸下了被狂風吹倒的大樹的巨根,帶回了家裡。(《雷暴》)
一個老男人,對著一張舊照片浮想。回憶海因茨,意大利某海濱小城的荷蘭榮譽副領事,一個笑口常開的充滿魅力的男人,如何因為一個神秘又美好的女人的死,而把自己慢慢折騰到死。(《海因茨》)
一個老女人,在孤獨中回憶自己愛的海軍中將,她好友的丈夫。閨蜜臨終時,他們告訴她,他們會在一起。他死後,能給她帶來某種短暫陪伴的,隻有那個餐廳裡的老侍者。他說不好英語,而她不擅於西語。他是個被命運詛咒的人,會偷走她的錢物。讓她不解的,是好友安娜貝拉在聽到他們會在一起時,竟是無所謂的樣子。(《九月尾聲》)
一個女插畫家,已故戀人是做金融的。他害怕黑夜,害怕傍晚,也畏懼陽光。他們都喜歡生活在外國。在他們的生活裡,曾有過幾隻烏龜。烏龜會喫落地的芙蓉花瓣。她最愛芙蓉,每天開出鮮艷的花,黃昏凋落。她畫過烏龜,寫過它們的故事,給它們取了基督徒的名字。她恨過他。他們相戀三年,分手沒多久,他就死了。對於她,他死過三次:離開,死去,被她遺忘。(《最後的下午》)
一個男人住在像個禪室般的頂層公寓裡,坐在僅有的一把椅子中,面對空白四壁,想念已故的寶拉。四十多年前,她曾上過《時尚》雜志封面,還因參加靜坐示威、街頭襲警和愛情派對上過報紙。她抽煙、酗酒,人見人愛。他跟朋友們都老了。他深情回憶與她相關的一切,可是她的形像是模糊的。他對她內心世界的認識,是具體而又模糊的。(《寶拉Ⅰ》)
他的回憶未能深入她的內心,寶拉的鬼魂卻聽到了他的召喚,認為這是默契。她描述了死亡的發生跟想像的不同,還揭示了他不需要伴侶,總是心有旁騖、虛無。而對於她的狀態,他一無所知。她愛他。她談論那些沒有愛情卻有激情的兩性關繫。他害怕黑暗。她知道狐狸總在他左右。沒人了解她。一切都是“轉瞬即逝。如同我們一樣不見蹤影”。(《寶拉Ⅱ》)
一個年輕女人,在風暴天氣去島上的海角。沒人知道她去那裡尋找什麼。她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解釋。她是去跳舞的,以風為舞伴,還想融入令她沉醉的狂怒大海,對海怒吼,以憤怒對抗憤怒。但這快樂無法與人分享。她相信自己是理智的,跟風暴、大海、這海角,擁有默契。(《海之角》)
現在,合上書,我的腦海裡留下的,是動蕩的海水。然後纔是那些閃爍浮沉的人與事。昏暗激蕩的海,是那些人物的背景,也是他們的舞臺。他們的回憶就像是舞臺上的一幕幕,始終貫通與縈繞著相似的氣息。盡管他們不是生活在某個海邊小城,就是生活在某座島上,不是在意大利,就是在西班牙,偶爾也會在阿姆斯特丹,回憶那些遙遠的海濱小城或是島嶼,可是空間上的差異並不影響它們最終生成這樣一部小說。
它們通過不同的人物命運和環境背景,從不同的角度探測著同樣的問題。無論他們的命運以何種方式在哪裡展現,其實都暗示著類似的生活狀態,那就是漂浮。這是諾特博姆始終著迷的主題。包括《萬靈節》裡的阿瑟,《儀式》裡的伊尼,其實過的也都是類似的漂浮生活。“唯一不變的隻有輕拂碼頭的大海,其餘的一切都可改換,是裝飾你記憶的道具。”
從根本上說,其實是他們的心,他們的靈魂,始終處在漂浮無依的狀態。甚至,對於他們而言,整個世界都是漂浮的,在動蕩不已的大海裡,而自己可能不過是漂浮的影子而已。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存在著,卻始終都是無根的。在生命的黃昏,他們試圖在記憶的深淵裡重新發現並抓住些什麼,結果不過是在努力重構的過程中又一次見證了個人世界那從未停止的持續瓦解的狀態。
在回憶中,他們似乎都想要證明自己是確實愛過的,但呈現出來的,卻是無盡的迷茫與疑惑,還有難以言說的苦痛:“當你走在燦爛的陽光下,你會驚奇地發現,生命的一切及其苦難,不過是在插滿尖玻璃的牆頭上行走。”
“當生命轟然倒地時,再看其是如何模樣。”
他們其實也清楚,自己的追憶所能企及的終歸不過是廢墟般的存在。同時,對於他們來說,或許廢墟還意味著所有外在之物被歲月消磨殆盡之後,某些真實本質的意外顯現。他們回憶是為了結束一段往事,盡管“結束與完結並不相同”。或許,對於他們來說,結束是為了讓往事以另外的某種方式重新存在,再也不會消逝,哪怕到了生命終了之時。而且,到了人生的黃昏,哪怕是憂傷也會變得彌足珍貴。
他們都是在回憶幾十年前的事。可是,他們比任何時候都充滿了不解與疑惑。他們的回憶,讓我們看到的是深淵,由人與人之間的,尤其是相愛的人之間的種種誤解與錯覺所生成。他們在回憶中拼盡全力所達成的,似乎也不過是終於抵近了深淵,而不是什麼答案。歸根到底,他們最後試圖做到的,不過就是如蒙塔萊的詩裡所說的那樣:“當生命轟然倒地時,再看其是如何模樣。”
作家在晚年喜歡追憶,會更多地觸及愛與死亡的問題,諾特博姆也不例外。這部小說裡的七篇作品,都是在追憶中圍繞著愛與死亡來展開的。那些人物都已是暮年,他們所努力追憶的人早已不在人世。隨著記憶力的衰退,他們的追憶已變得越來越艱難,唯一的動力,來自那些作為他們心結的已故之人。人在年輕時總是充滿激情和想像力,容易自以為是地把對情感關繫的沉浸等同於了解一切,完全看不到其中的盲目性。在即將抵達人生終點之前,回望那漫漫長路上已然模糊的一切,除了發現種種迷惑依舊難解之外,還會忽然發現,哪怕是迷惑,也是極為珍貴的,如同永恆的星辰,在遙遠的過去閃爍著迷人的微光。而哪怕那些與愛有關的追憶都是以死亡為背景的,所謂生命的樣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那些曾經的愛戀時刻勾勒出有光的輪廓的。
在《貢多拉》裡,男主人公早年在威尼斯為那個來自美國的、有意大利名字的少女著迷。那個笑稱自己是個女巫並喜歡在信裡“長篇大論地談著魔法和巫術”的少女,那個即使是在熟睡的時候也會“帶著鮮明的、野獸一般的驕縱”的少女,隻是用“她那藍灰色的眼睛如何在黑夜裡熠熠閃光”就將他捕獲了。她給了他人生中最為短暫而又強烈的愛情體驗,讓他終生無法釋懷。她就像個小仙女一樣降臨,占據了他的心。然後她走了,變成了女人,結婚生子,然後離婚搞藝術,還差點出家。但對於他,她就像是偶然照入他生命的一束強光,隨後留給他黑夜。他本以為在她生前的那次美國重逢可以讓他結束黑夜狀態,卻沒料到她後來的死會把這黑夜推向極致。“某些人就此從你生命中消失,這真讓人難以承受。你非得有百倍的人生同時展開,纔說得過去。”話可以這樣說,但真要面對卻是無比的艱難。“死亡本是自然的禮物,卻時常會帶來如臨深淵的傷痛,你恨不得自己也墜入深淵,向死亡之謎的慘淡與真實投降認輸。”或許,諾特博姆試圖通過這樣的一篇小說向我們暗示,真正的愛,其實就跟死亡一樣,在本質上都是終極性的。
而在隨後的那篇《雷暴》裡,諾特博姆則為我們展示了愛人之間難以理解甚至充滿誤解的一面,以及死亡如何以偶然一擊照亮真相,同時又像影子似的追隨著相愛的人們。那位木刻藝術家因為黑膽質性格導致的害怕鼕天和陰冷天氣,其實隻是表面的,從本質上說,他總是敏感於死亡的存在和隨時切近。他理解不了女友可以絲毫不受環境變化的影響,專注於那些在他看來無趣的事。她的健康穩定正是他所需要的平衡之力,就像錨一樣,能助他避免被黑暗動蕩的海水吞噬。那位沉迷於拍攝閃電的美女跟情緒糟糕的男友,就像是藝術家跟女友的關繫狀態的放大版映像投射。那個男人在惱怒中走向海邊並意外被閃電擊中而死,就是個像征,是那個情緒穩定的美女導致了這個悲劇後果。但他也知道,這其實隻是個意外,那個被閃電擊中的男人,那棵被大風撥根摧倒的路邊大樹,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命運。那是死亡之力的突現。他之所以要鋸下那像美杜莎的頭顱似的龐然樹根,並把它帶回家裡收留,與其說是出於藝術的需要,不如說是試圖暗示阨運並非總能掌控一切。或許,他確實想努力活下去,做一個幸存者,在死亡的邊緣。但,也僅僅是或許而已。“別把它燒了,他說。讓它干燥干燥。在晨光裡,她能看到這塊木頭最終會變成什麼模樣。”似乎,這樣的句子已對這對戀人的未來做出某種暗示,並沒有人能逃脫自己的命運。
從某種意義上說,《海因茨》就像是《貢多拉》和《雷暴》的強烈變奏曲。如果說後兩者看起來有點像首小提琴獨奏曲的話,那麼前者顯然更像是氣勢迫人的鋼琴協奏曲,關於絕望的愛與個人的秘密。那個在小說裡從未出場的“真如春光一般明媚”的“超群脫俗”的女人,阿莉爾,就是秘密的核心。或許,正是海因茨對她過於狂熱的愛意外導致了她的死。可是誰又知道呢?她的墓志銘是這樣的:“阿莉爾·範·德·盧特,人生隻在須臾,本來寂靜無聲,1940—1962。”這段話本身就是個謎。當愛的對像死了,這狂熱的愛就像失控的強力又轉向了愛者自身,就這樣,海因茨的餘生就是把自己那原本像克拉克·蓋博般瀟灑的形像一路折騰得臃腫走形、令人不忍直視,又折騰到死的。沒人知道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強烈的愛使人成其所是,也會剝奪人的一切。跟死亡一樣,這愛會讓命運瞬間顯露其真面目。愛與死,都是生命的終極秘密。與此相比,敘述者那始終充滿耐心的淡定追憶,盡管本身也像個秘密,卻還是有些微不足道了。或許,原因並不復雜,隻不過是他終其一生也從未抵近過那種強烈的愛的狀態,既沒被愛成其所是過,也沒有被愛摧毀過。就像這篇小說前面引自艾維·康普頓—伯內特的《最後的與最初的》裡的對話所暗示的那樣,他人生的關鍵詞可能也就是“空洞”“毫無意義”。而且,最好還是接受這個事實吧,“如果本來就無一物,我們不必假裝好像有東西似的”。
相形之下,《九月尾聲》跟《最後的下午》看起來更像是插曲。前者是個獲而一無所獲式的故事,寫蘇茜孤獨晚景中的淒涼與追憶。當年她在好友安娜貝拉臨終時,跟後者老公海軍中將一起向這個將死的女人坦白,他們會在一起。讓她始終不懂的,是安娜貝拉為什麼會對此事無所謂?或許,她應該明白卻未能明白的,是在死神降臨之際,人有可能會寬容一切。或許,她能明白的是,比喪失所愛和死亡更難以承受的,是在孤獨中等待死神到來的煎熬,當然,這煎熬同樣也有可能讓人寬容一切。《最後的下午》是關於恨的。恨的前提,仍舊是因為愛和不解。那個女插畫家對曾相戀數年的戀人的恨意難消,與其說是因為情斷,不如說是由於他讓她陷入難以理解的茫然境地。因為恨,她讓他死三次,最後一次是遺忘。可她真的會遺忘嗎?很可能他反而在她心裡永遠活著,而背景卻是互不理解之謎。誰又能說,當初她給他的那次報復行動不是他的死因呢?或許,她隻是想完全擁有他,結果卻是毀了一切。
如果說《貢多拉》、《雷暴》和《海因茨》這三個樂章都是以男性視角來展開的敘事,而《九月尾聲》和《最後的下午》則是以女性視角的敘事,那麼,在《寶拉Ⅰ》和《寶拉Ⅱ》裡,則是通過男性和女性兩個視角共同完成的二重奏式敘事,就像是一問一答。《狐狸在夜晚來臨》這個書名,即是出自《寶拉Ⅱ》。這兩篇的對應關繫,以及狐狸意像的雙重隱喻:神秘率性的自在與死亡,在諾特博姆那裡當然是有深意的。一方面,他試圖通過這兩篇彼此密切相關的小說來暗示愛情關繫裡男女之間的種種誤解與錯覺;另一方面,他又似乎想通過對這一切的呈現,基於人的晚年狀態和鬼魂狀態,展現這樣一個事實:即使有那麼多的誤解與錯覺所造成的隔閡深壑,愛,畢竟也曾還是真實存在過的,但是,從本質上說,它也跟生命本身以及與生命相關的所有現像一樣,都是虛幻的,像幻夢一樣。在這裡,我們似乎可以意識到,寶拉,作為鬼魂的寶拉,完成的是作者賦予她的揭秘使命。在小說結尾處,她對他的最後告別,隱約間有種禪宗公案的味道。
作為整部小說的尾聲出現的《海之角》,與其說是篇小說,倒不如說更像是首散文詩。它充滿了像征意味,就像是諾特博姆對其女性觀的詩化呈現,或是他獻給女性的精神禮贊。在其他篇小說裡出現過的那些女性角色的所有生命與精神的秘密,似乎都可以通過此篇來做出揭示。她是一個女人,也是所有女人。海角,就是大地與海洋的臨界點,是平穩的日常世界與動蕩的異常世界的分裂與交彙之處,也是女性生命與精神之力跟神秘的自然偉力對話之點。在這裡,她展現的是生命之舞,是如此強悍的生命與精神的存在狀態,她不是在對話,而是在咆哮,面對動蕩而又危機四伏的深淵大海,她要“融入這令人沉醉的狂怒中”。
我來這裡就為此:
為了咆哮。
我鼓起勇氣——我
知道這裡沒有人能看見我,
聽見我—我向大海
咆哮,反擊,
剛開始我心存懷疑,
聽不見自己的聲音,可隨後
我的吼聲越來越響,
以憤怒對抗憤怒。
我像一百隻海鷗一樣尖叫,
我向著溺水而死的水手們大喊,
發出呼喚,他們也會回應,
我知道這就是我的渴望,
渴望著迷失在這起伏的律動之中,
但我深知這不可能,舞蹈
就此結束,我要步履沉重地
走上回頭路,風暴呼嘯,
追趕著我,疲憊地拖累著我。
我已經丟失了北方,
我們這會兒這麼說,丟失了
屈拉蒙塔那風。這就等於說你
已經失去了理智,當然了,
對我來說,這並不對,
我的理智一點也沒少。
我很快樂,卻無人可與我分享。
我隻有等到風暴和大海再次
將我召喚到海角去,
這是我們的默契。
把小說結尾部分做分行處理之後,它們就是諾特博姆為女性的精神意志之力寫下的贊美詩。想想看,出現在《雷暴》中那個叫羅塞塔的女人的所思所想難道不也是與此狀態相近似嗎:“現在他就像是黑暗大海中隨意漂泊的孤舟。她知道自己的平靜讓他更加惱火,她也知道,在面對他所自稱的黑膽質脾氣時,也隻有自己的淡泊堅忍能讓他支撐下來,面對更黑暗的季節。對此最好的辦法不過是迎頭而上。”這是她的愛,是她的愛的方式。而那個叫魯道夫的男人,那個木刻藝術家,盡管也會說“我想要的,就是不羈的自然之力”,可是他具體表現出來的狀態其實要明顯脆弱無力許多。或許跟這部小說裡的很多男人一樣,他不是以反諷的狀態想著“人生多美妙,應當一次又一次地巧加裝點”,就是“我想要個解釋,可總也找不到”。關於這一點,或者說關於男人,寶拉看得非常透徹:
“你從來就沒有懂得我們之間的關繫。你相信了我說的謊言。女人善於撒謊,而男人善於被騙,哈!與你繼續在一起就意味著我不得不苦苦忍耐你一貫的心有旁騖。這太痛苦。所以這麼多年以來,你還是孤身一人,我當年一眼就看出來了。你存在於世,根本不需要伴侶,與你共同生活將會是一場災難,我能挺過這災難,而你不行。你活著,就是為了心不在此,或者說,你心在此,而人已經不在這停留。”
記憶、照片或諾特博姆的敘事藝術
諾特博姆深諳記憶的本質以及回憶的重構屬性。他顯然清楚,所謂的記憶與回憶,其實都是基於“當下”而發生的,甚至可以說人就是立足於“當下”來完成對記憶的不斷重構。而照相之於記憶與回憶來說,與其說是在場的證據,倒不如說是以某種貌似平常卻又異常突兀的方式揭示了記憶本身斷裂無序與殘缺的本質。也正因如此,他纔會說:“好的故事裡,‘當下’既無處尋覓,而又無所不在。在照片中,‘缺席’是重要的,至於多麼重要,卻無法付諸言語。我是說,如果你從來就不認識照片中的人,你也不可能知道誰缺席了,這就是重點所在。”
對於諾特博姆這樣的作家來說,哪怕一張看似極普通的照片,也足夠用來生成一個關繫微妙且意味深長的多重戲劇的現場。他所創造的戲劇呈現方式,卻並非按照慣常邏輯展開演繹式的,而是像做切片試驗一樣,把每個人物的不同側面,從內到外,由淺到深,從具體到微妙,以半透明的狀態層層疊疊,每一片之間固然有些空隙,但也正因如此,所謂的戲劇性纔擁有了不斷流變生成的空間。當然這樣來形容也容易產生誤解,仿佛那些切片都還有其靜態的一面,就像照片本身所呈現的那樣,但實際上,這一切都是流動的,就像河流,時清時濁,滾滾向前,而其中的敘事者,則是遊於其中,時潛時浮,每個敘事層次的生成與變化,都好像隻是沉浮的轉換,隻有細心的讀者纔能真切地體會到那河水的明暗與動蕩。
在諾特博姆筆下,即使是對話,都明顯有些像獨白—交替發生的獨白。從質地上說,這些貌似獨白的對話跟意識的流動,以及場景、細節的微妙流動與變化,其實並無清晰的界限,而這似乎也正是他所要追求的敘事效果。面對這個世界,無論是虛構的,還是真實的,隻有在這樣的效果裡纔會真正做到敘事的水乳交融,除了讓人沉浸其中之外,再也不需要任何意義上的區分,什麼是真的,什麼是虛幻的?根本不需要區分,說到底也根本不會存在這樣的界限。
每一次,當你從諾特博姆的這部小說裡忽然抬起頭來,回想著小說裡發生並展現的一切,除了會想到愛、死亡與命運,還會想到些什麼呢?你知道,這裡不可能會有完整清晰的故事,不可能會有對那些秘密的最終揭示,即使你能以非同尋常的定力和敏銳度去凝視那些漂浮在異國他鄉的人的命運如何顯露真相,也不過是像獨自面對黑夜裡激蕩不已的大海,你能感受到那奔湧而來的氣息,能嗅出氣候變化的味道,能意識到它有多麼像人的內心世界和命運的隱喻,也能感同身受,卻永遠都不可能說明這一切。而這些,或許也正是諾特博姆的小說敘事藝術的本質特征。
“這就是結局嗎?當然不是。這是真實的生活,毫無線索也沒有情節。”
2021年5月16日於上海 查看全部↓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