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法律與文學:從她走向永恆 | | 該商品所屬分類:圖書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 【市場價】 | 529-768元 | | 【優惠價】 | 331-480元 | | 【作者】 | 瑪麗亞·阿裡斯托戴默 | | 【出版社】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 【ISBN】 | 9787301284285 | | 【折扣說明】 | 一次購物滿999元台幣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2000元台幣95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3000元台幣92折+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4000元台幣88折+免運費+贈品
| | 【本期贈品】 | ①優質無紡布環保袋,做工棒!②品牌簽字筆 ③品牌手帕紙巾
|
|
| 版本 | 正版全新電子版PDF檔 | | 您已选择: | 正版全新 | 溫馨提示:如果有多種選項,請先選擇再點擊加入購物車。*. 電子圖書價格是0.69折,例如了得網價格是100元,電子書pdf的價格則是69元。
*. 購買電子書不支持貨到付款,購買時選擇atm或者超商、PayPal付款。付款後1-24小時內通過郵件傳輸給您。
*. 如果收到的電子書不滿意,可以聯絡我們退款。謝謝。 | | | |
| | 內容介紹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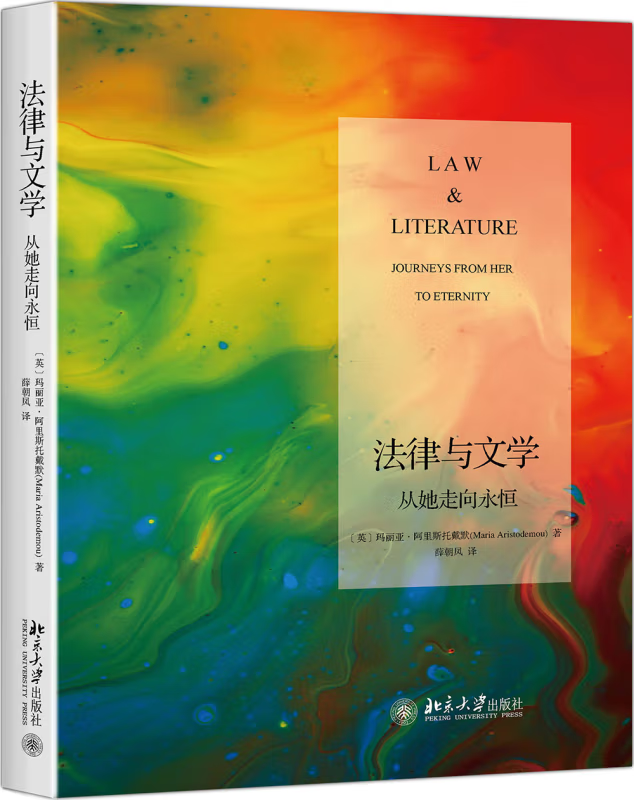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ISBN:9787301284285 版次:1 商品編碼:12150499 品牌:北京大學出版社 包裝:平裝 開本:16開 出版時間:2017-07-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384 字數:418000 代碼:59 作者:瑪麗亞·阿裡斯托戴默
" 編輯推薦 《法律與文學:從她走向永恆》語言富有哲理與詩性,不僅優美且見解獨到。
本書前十章都是對小說文本的解讀,內容豐富。
本書基於大量文本資料,探討了文學與法律的關繫,生命與永恆的價值。 內容簡介 “法律與文學”的學科交叉研究被認為是近三十年來出現於北美和英國的跨學科理論研究。《法律與文學:從她走向永恆》從實踐中一起兇殺謎案入手,分別從“起源的神話與神話的起源:超yue俄狄浦斯之旅”“作為婦女再造詞語的劇院:朝向埃斯庫羅斯《奧瑞斯提亞》的肉體之勝利”“《以牙還牙》中死亡與欲望的婚姻”“差異前後的世界: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嘯山莊》”“感觀世界的法律:加繆的《局外人》”等文學作品中探討法律和文化的關繫。 作者簡介 瑪麗亞·阿裡斯托戴默(Maria Aristodemou),劍橋大學法學碩士,現任教於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主要著作有《法律、精神分析與社會:認真對待無意識》(Law, Psychoanalysis, Society: Taking the Unconscious seriously)等。主要研究興趣包括法學與精神分析理論實踐、法學與文學、法學與電影以及法學與音樂等領域。 精彩書評
本書開創了法律文學批評研究的新時代,是一本繫統性地、深入淺出地也是寓教於樂地研究法律中文學形式的著作。我強烈推薦大家閱讀此書,並極力推薦在法律和文學的教學課堂上使用此書。我建議首先從最後一章即“重新開始”讀起,不僅因為這一章文字優美、蕩氣回腸,而且因為這一章是整本書之所以行之有效的開篇序言。
——彼得·古德裡奇,紐約葉史瓦大學卡多佐法學院法學教授
(Peter Goodrich, Professor of Law, Cardozo School of Law, Yeshiva University, New York)
本書論述詳實,文字激昂,在法律文學研究領域實屬翹楚。縱覽全書,行文高雅流暢,見解獨到鮮明,論證強勁有力,洞幽燭遠,辭微旨遠,真知灼見遍布字裡行間。我深信此書將會吸引世界各地讀者的眼球而且將影響深遠。
——邁克爾·弗裡曼,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英格蘭法教授
(Michael Freeman, Professor of English Law,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目錄 第一章 開端……虛構現實,一個短篇謀殺迷案
第二章 起源的神話和神話的起源:超越俄狄浦斯之旅
第三章 劇院裡女人重演人世間:埃斯庫羅斯《奧瑞斯提亞》的血肉之軀走向勝利
第四章 《一報還一報》中死亡與欲望之間的婚姻
第五章 差異之前的世界與超越差異的世界: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嘯山莊》
第六章 感官世界中的法制:論加繆的《局外人》
第七章 女性作為立法人的奇幻小說:安吉拉·卡特的《血室》是賦權還是誘捕
第八章 逃過火災的檔案熱:《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中的法律記憶以及其他文本記憶
第九章 托尼·莫裡森《寵兒》的語言、道德和想像力
第十章 “努力夢想”:博爾赫斯小說中女神的夢想
第十一章 重新開始:身陷迷宮的律師以及“從她走向永恆”
索引 查看全部↓ 精彩書摘 第一章 開端……虛構現實,一個短篇謀殺迷案
我們生活在一個由各種虛構主導的世界——大宗銷售,廣告,像做廣告一樣做出來的政治,電視熒屏造就的對經驗世界任何最初回應的搶先占有。我們生活在一個鴻篇巨制的小說裡。如今,作家已經越來越少需要創造其小說中虛構的內容。虛構早已存在。作家的任務就是要創造現實。
——巴拉德(J. G. Ballard)《撞車》(Crash)
第一節 敘述性回避、奇幻小說與等級制度
法律和文學的本體論地位是什麼?或者,按照拉康(Lacan)的說法,“真實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思議的,什麼是法律和文學可以想像出來的地位?然而,我們贊同法律和文學不同,法律是處理生與死這個物質世界裡的東西,法律和文學二者首先都是書面的符號。法律世界和文學世界都是詞語的定義和存在所建構起來的,並且依附於後者。就是這些詞語創造了不同的虛構的世界,而這些世界看起來又是那麼不可避免。
任何企圖通過法律或者文學的符號和語言來管理世界,企圖俘獲、馴化和統治這個如迷宮般復雜的世界都是枉費心機,這個世界的起源、設計及其設計者,我們都無從知曉。法律和文學都是人為的構念、人為的概念或者人為的抽像化,如同時間或身份一樣,它們意在從混亂中創造出秩序,特別是律法方面,意在強加自以為是的秩序:對於當事人的身體乃至其靈魂深處進行書寫,以便實現且取代他們無法實現的欲望。在這個書寫過程中,這些企圖成為他們自己的迷宮,不僅對於那些想要闖入該迷宮的人,同時對於他們本人而言都是迷惑難解卻又明心益智。
然而,藝術家承認甚至有時候就是要吸引大家去關注其構造物的偶然性和人造性,可是律法語言卻要竭力掩飾其人造痕跡。雖然藝術家坦白承認自己的作品是任意的、不完整的、假定的和臨時的,但是律師卻堅持假裝他們是自然的、必然的,堅持認為他們不僅可以提供所有答案而且能夠提供所有正確答案。因為他們渴望信奉原始點論,他們相信這個世界是有開端、中端和終端這三端的,這個世界的運行有規可循,清晰可辨,並且結果也是可預見的,對此他們深信不疑,如同這個世界本身是不可知的一樣都牢不可破。
我們對過去的無知、對現在的不解以及對將來的擔心,無論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都促使我們無論是作為法律和文學的作者還是讀者努力認識並進而掌控我們的世界。所有這些閱讀和寫作都是在欲望中發生,在我們對他人以及他人欲望所產生的欲望中發生,拉康的鏡子賦予我們充實感並且幫助我們奪回我們丟失的豐富童年。故事在這樣的尋求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通過故事我們試圖回憶過去,應對當下並展望未來,我們創造故事來掩蓋我們所不了解的和無法接受的東西。對敘述的渴望,對開端、中端和終端的渴望,就是對於我們那不堪一擊的身份的自我識別和確認。法律和文學的寫作以及閱讀給這個缺乏根基的世界臨時提供了已被錨定的幻覺。然而,真相、統一以及終止隻會帶來自我的解體,帶來隻有死亡纔會有的最終結局。
很久以前,亞裡士多德(Aristotle)稱贊敘述和悲劇特別具有淨化的能力,因而能夠撫慰聽眾和觀眾心中的恐懼和悲哀。敘述是理解我們自己以及我們所處世界的一種方式,渴望敘述不僅對於悲劇至關重要,而且對於所有敘事作品同樣重要,無論這些敘事作品是法律的、文學的還是法律文學的。有關法律起源及終止的那些理論,有關正義、自由、權利、判決以及解釋的那些理論,它們共同參與管理我們世界的企圖,企圖將潛在的混亂縮減至可控範圍之內。想要在我們的信仰、詞句以及行動中發現意義的企圖似乎沒完沒了,這些企圖反映了我們妄想找到一個根基,一個超驗的能指去對抗我們對於未知的恐懼。觀念、理論和神話在這個方面有著特別的作用:它們都是人類的成果(或許如同我在最後一章所提出的它們是男性的),渴望秩序和共性,渴望起源和目的,減少混亂和異質,減少對於已知的差異,最後達到天下大同。
不過,沒有哪個敘述是完整的,總會有缺口、沉默和無知。敘述看起來解決了矛盾,而矛盾的存在又第一時間導致了敘述的必要性。線性敘述似乎非得有個結論,當它們再給出答案時似乎就給出了新的答案,而這些答案總是早已預先假定的。敘述因此發明了而不是反映了我們的生活、我們自己以及我們的世界。不論是法律的還是文學的還是就像我們這本書所探討的法律與文學的,敘述不是中立的:它們在追究、揭示和創造意義,並且將意義合法化。
進一步來說,在我們文化中有些敘述相比其他敘述享有特權:詩歌從哲學中脫穎而出,倫理學從美學中脫穎而出,理性從情感中脫穎而出,法學從文學中脫穎而出。在法學教育中,關於法律的起源、功能和需求,法官和法律哲學家對此的敘述要比其他敘述更有說服力。特別是哲學,它聲稱最有資格告訴別人說什麼做什麼、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什麼是合理的什麼是荒唐的。在柏拉圖(Plato)看來,外行對於社會的認識不足信,因為外行既沒有纔智也沒有閑暇去判斷對錯。哲學否定了門外漢的知識,並以追求真理為名為社會等級的分化作辯護。小說、修辭以及文學都認為自己關乎文體和哲學,同時它們也都認為自己是追求永恆真理的獨立學科,即便不能超越神學也是有別於神學的。反過來,哲學家是知識的“載體”而不是觀點或信仰的“載體”,他的工作不是藝術家所做的事情,而是立法者所做的事情,是給人類的理性制定法律。
不過,企圖把哲學從文學中獨立出來維持它的優越話語地位是注定要失敗的,因為即便是哲學也無法奢望脫離語言。哲學自身的定義和存在是通過把自身區別於其他類型的語言,特別是小說的、文學的和修辭的語言。哲學雖然聲稱是要宣告那些無可辯駁的真理,但是也隻能通過忽視語言的本構性和隱喻性的本質來作此宣告。德裡達(Derrida)對於哲學的基礎主義的批判取代了哲學和文學的界限:那些想要寫哲學論文的人所使用的語言以及所選擇的語言形式是無法與哲學內容分開的;相反,文學文本以及文學評論作出了大量哲學式的假定,跟那些聲稱要做純哲學式的寫作一樣多。德裡達揭示了語言是如何使那些探求真理和存在的哲學家們分心甚至感到沮喪,並且由此得出結論認為哲學、政治理論當然還有法律都是以與文學相同的方式發揮作用。
哲學依賴語言意味著它不再比其他的語言形式優越,因而也不再聲稱是構成其他學科的基礎。特別是在解構的和心理分析的詮釋中,這個據說是純粹的、自我參照的語言再次回來,不斷指涉文本的統一性、連貫性和獨立性。隨之而散的還有法律和理性的專橫,哲學家和立法者都無法掙脫修辭抑或文學:與所有作者一樣,他們都是任由語言擺布,對語言我們既不擁有也未掌控。
我們區分各種不同的閱讀、寫作和學習,我們區分各種不同學科,這都是法律文學研究的靈感的一部分,我們的區分因而是文化上的而不是自然的,我們是在建構而不是在施舍。這樣的區分由我們語言實踐活動創造出來,與此同時也依靠我們的語言實踐,並且作出這些區分的人認為自己對真理的表述比其他人的表述都要優越,所以這些區分是分層次的。這個研究贊同我們當下的懷疑,即我們對於任何一種試圖發現“真理”的方法、故事、理論或者學科都不信任,這不僅是因為後者隻不過是掩蓋權力鬥爭的一種幻像,誰有權誰就界定我們所在的世界,人們對此鉤心鬥角。尼采(Nietzsche)重新回到審美體驗,這不僅有啟發性而且也很有價值,福柯(Foucault)對於人文科學的批判以及德裡達對於哲學中基礎主義的抨擊都是重寫了詩學與哲學由來已久的恩怨。柏拉圖發起了這場爭辯,對此他的解決方式就是把詩人從他的理想王國中驅逐出境。不過,這場爭辯的解決使哲學付出了代價。自柏拉圖以來,一代又一代的哲學家們熱衷於為哲學開拓出單獨的角色,即作為真理的仲裁者,他們使用與詩學相同的技藝,卻對詩學技藝大肆詆毀,隻為達到自身的目的。總之,法律一直以來早就是文學的,同時文學一直以來早就是法律的,對此我即將論述。
企圖將哲學和法律從文學中區分開來,正如我這本書最後一章所指出的,就是企圖將女性從法律迷宮中排擠出去:尼采訴諸美學並沒有妨礙他宣稱女性是真理的敵人。相反,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就是一代又一代男性哲學家的一位代表,他將自己的研究看作努力去證實抽像的語言、理性和常識,藉此來抵抗女性遊戲、引誘和欺騙的語言所帶來的誘惑和禍害。因此,正如德裡達所認為的,“把藝術、風格和真理的問題與女性的問題分離出來”是不可能的。
男性律師偏愛抽像的語言、理性和智力也是企圖否定觸覺的、身體的和感官的東西:據說他們是通過克服詞語來抑制女性用身體繁殖的能力,然而實際上正相反,他們是通過模仿詞語來抑制女性用身體繁殖的能力。也就是說,否定每個人的“第一個家、第一個身體、第一個愛”:母親。 查看全部↓ 前言/序言 譯者序
法,在西周金文中寫為“灋”,《說文解字》中這樣解析:“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廌,乃神獸,“解廌,獸也。似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像形,從豸省。凡廌之屬,皆從廌。”由此可知,法之意義在於維持公平正義,其手段在於法器,如遠古傳說中的“廌”和“復仇女神”,也如當今現實社會中的“司法繫統”等國家公權力機構。
法律,無論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都是由“天賦神權”的神之法逐漸演變為“契約精神”的人之法。在中國,封建王朝的歷代天子們自詡為“天神之子”,代理天庭履行神授君權的天神之法,如西周開始的“親親尊尊”的宗法禮制,秦朝推崇的“嚴刑峻法”的法家思想,漢朝獨尊的 “三綱五常” 的儒家法律思想,這些替天所行的“道”在宋明理學時期被發揮到了極致——“存天理,滅人欲”。如此宗族禮教制度,是中國古代法律思想的具體表現形式。跟這種天子法律代理制度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是西方社會的人神共治,希臘神話中奧瑞斯提亞弒殺至親遭復仇女神追究,直至雅典娜在戰神山設立雅典娜法庭審判此案纔得以平息,雅典娜法庭的成立標志著法律由神之法開始走向了人之法。從此,由自然法、神之法衍生出成文法、人定法,諸多法門正是為了“觸不直者去之”,以期實現托馬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的“趨善避惡”(that good is to be done and promoted, and evil is to be avoided)。托馬斯·阿奎納在論述自然法時指出,自然法建立在一些“首要原則”基礎之上,“趨善避惡”是首當其衝的第一準則。
東西方社會在商品充分發達、交易頻繁發生的同時逐漸滋生出契約精神,買賣合同的出現基本保障了交易的有序推進,此時,個人作為法律主體的地位逐漸得以確立。交易合同的簽訂是法律發展史上繼雅典娜法庭成立之後又一個裡程碑式的跳躍,從此,人的自我意識開始獨立於神的旨意,法律由保護神的旨意更多地傾向於保護人的意願,於是法律實用主義大行其道,這也給人類帶來了更多的關於情、理、法之三角關繫的困惑,蘇格拉底之死是人之法開始獨立於神之法的一個投名狀。
法律,是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是反映了統治階級意志且依靠國家公權力機構來實施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範。法律的本質在於階級性,在於一時一地的統治階級的統治約束力,而文學的生命力在於想像,想像不受時空的約束。如果說文學是一個筋鬥十萬八千裡的“孫悟空”,那麼法律則是企圖規範心猿意馬的“緊箍咒”,然而,法律本身也是一種欲望,是統治階級的統治欲望,跟其他欲望相比,法律這種欲望具有強制性、普遍性、歸約性以及時空性,法律是想要對欲望加以控制的欲望。
文學是作者通過語言文字表達作者思想情感、反映社會現實的語言藝術作品,按體裁分類,文學主要有詩歌、散文、戲劇和小說等,文學與宗教、哲學、法律、政治等都屬於社會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領域。文學離不開語言,也離不開語言的想像,想像是文學創作的心理機制。
想像,是一種心理活動過程,是人類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這種認知方式可以根據現有事物的表像進行加工創造,或者根據已經認識的事物規律進行合理的邏輯判斷和預測。想像,可以不受時間和空間的束縛,包括有意識的想像(如文學創作)和無意識的想像(如做夢)。想像是認清事實和發現真理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從某種角度上說,事後證明為真實可信的想像即為真相。對於真相的認識和表述由於感知和想像的不同而表現不一,如盲人摸像,也如小鎮居民對於聖地亞哥被殺當天天氣的回憶。真相,是像一堵牆,還是像一根繩索?真相,是陽光明媚,還是細雨迷蒙?如果真相就是“大像”或“天氣”,那麼每個摸大像的人和每個回憶那樁兇殺案的人都認為自己認識的和表述的就是真相。認知的局限性和表述的片面性表明,人們自以為是的真相不過是假像,是虛妄。如果真相和真理果真存在,那麼隻有那個“阿萊夫”(the aleph)纔能認識和映射出它們,因為“阿萊夫”雖小,可是卻包含了整個宇宙。真相彌諾陶洛斯或許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說彌諾陶洛斯真的被殺死了,那麼幫助忒修斯殺死彌諾陶洛斯的不僅是阿裡阿德涅(Ariadne)的線團,更是那個“阿萊夫”。
顧名思義,法律文學主要研究法律中的文學和文學中的法律。法律與文學兩者都是借助語言來表達和理解人和事的問題,區別主要在於,文學中的那些人和事可以是虛構的,而法律中的那些人和事則通常確有發生,法律對於言行有一定的約束力,文學卻可以超越現實世界的束縛且能拓展意識的自由空間。法律文學通過認知能力特別是想像力告訴世人,文學作品中的法律思想、法律知識和法律技術可以是現實生活中法律體繫的基質、發展和升華。希臘神話中所敘述的復仇、審判和亂倫禁忌正是西方法律制度的緣起。法律體繫通過公權力機構維持社會秩序,從而企圖控制眼耳鼻舌口身的欲望,文學作品通過語言文字明辨是非,引導心靈和意識去體驗美學的享受。欲望本無善惡之分,可是欲望的滿足不可以不擇手段,個人或法人的欲望原則上需要受到法律制度和倫理道德的規約,如果欲望在實現的過程中侵犯了他人的權益或者違背了社會的公序良俗,那麼欲望的主體則當受到法律和道義的懲罰。在司法實踐和法理研究中,對欲望的研判不容小覷,如犯罪動機是量刑輕重的一個考量因素,犯罪心理學在犯罪動機和作案心理活動等方面的探究對於預防犯罪、懲治犯罪和矯正罪犯有著一定的意義,這些當然也是法律文學描寫和論述的一個主要內容。然而,法律所懲處的欲望隻能是已經導致既成犯罪事實的顯性欲望,腹誹罪的廢除是法律的一大進步,法律文學通過對於文學作品中犯罪起因、情節和結果的描述不僅可以揭示顯性欲望還可以揭示更多的隱性欲望。另一方面,如果欲望長期得不到滿足,這反過來也可能會導致發生犯罪事實作為欲望的一種代償式滿足。法律意在通過理性來疏導和控制非理性的欲望,欲望和理性都是通過意識這個介質產生的,法律和理性對於欲望的控制歸根結底是借助意識的參與纔能產生作用。
意識也是認識客觀世界的基礎。中國科學院院士朱清時在介紹量子力學的時候聲稱,“人類的主觀意識是客觀物質世界的基礎——客觀世界很有可能並不存在!”這種觀點是對“薛定諤的貓之思想實驗”(Schrdingers cat thought experiment)以及物質波理論最直白的解釋,即意識是量子力學的基礎。客觀世界在意識作用之前處於一個疊加狀態(superposition),如貓既死了又活著,而一旦意識參與進來,客觀世界就處於坍縮狀態(collapse),則貓要麼死了要麼活著,不可兼得。意識就是這樣通過波函數坍縮來改變客觀世界。路易·維克多·德布羅意(Louis Victor de Broglie)的物質波理論指出,一切物質(包括光和實物粒子)都具有波粒二像性。由此可見,物質和精神都是波動的現像,區別在於波動的頻率不同,眼耳鼻舌口身所感觀到的,是物質現像,而心靈和意識所識別的則是心理現像。現像來源於意識,即念頭,物質是意念累積的連續相。念頭無處不在,念頭遍法界虛空界。念頭也無時不在,彌勒菩薩說,一彈指三十二億百千念。認識客觀世界,就是認識所有呈現在時空世界裡的現像,也就是認識人類自身投射時空裡的觀想行識。量子力學創始人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早就斷言,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物質這回事,因為物質是個幻像,是意念累積連續產生的幻像,也就是常說的心有所念。意念之多變化之快,導致了對客觀世界和事實真相的認識存在著太多不確定性,正是這個不確定性纔是人類痛苦的根源,對於人類而言,唯一可以確定的真理恐怕就是人類向死而生。於是阿波羅下達法令:“人啊,認識你自己吧!”
《法律與文學:從她走向永恆》主要從女權主義角度分析了西方經典文學藝術作品中的法律思想、法律現像、法律問題及其表達方式,揭示出西方法律一直在為父權法律背書,女性是父權法律得以建立的犧牲品,也是維持同性交往社會關繫的交易對像。《法律與文學:從她走向永恆》不僅是一部揭示了女性在父權法律社會遭受壓抑的“她史”(herstory),也是一部研究法律文學發展的鴻篇巨制。該論著研究語料豐富,包括西方經典戲劇和小說等文學著作、流行音樂、影視作品以及南美魔幻現實主義作品;研究對像的時空跨度極大,從遠古的希臘神話到當代的文學藝術,從歐洲到美洲。本書作者瑪麗亞·阿裡斯托戴默(Maria Aristodemou)是全英國開設“法律文學”(Law and Literature)這門課程的第一人。她認為法律,即父權法律,隻會導致更多的謀殺—復仇—謀殺的循環,死亡纔是它的唯一歸宿,因為法律有意抑制了女性的法律主體地位,法律是走向法律它自己的旅途,人類的成長就是俄狄浦斯的回家之旅。於是,作者呼吁創造另一種語言即女性語言去書寫另一種法律即女性法律,當女人不再映射男人所需的自我滿足反而是女性自身欲望的時候,就更加迫切需要這種新法律即女性法律,當女人開始在黑夜為她自己書寫的時候,也就是女性法律得以建立的開端,跟著她纔能走向永恆。
《法律與文學:從她走向永恆》全書共有十一章,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四章,旨在揭示女性是父權法律制度這個迷宮建立的起因、女性是法律迷宮排擠和吞噬的對像,同性交往的父權社會害怕差異性、害怕模仿、害怕女人,為了維護同性社會交往的秩序、為了控制欲望、為了避免亂倫禁忌,法律應運而生,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反映了父權意志,是男人欠缺生育能力的一種代償。第二部分包括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旨在揭示女性法律主體意識的覺醒和抗爭歷程,女性在父權法律面前長期以來隻是局外人,被迫保持沉默,充其量不過是法律制度的裝扮物,“讓法律迷宮蓬荜生輝的第一批尸體就是女人的尸體:一個慘遭殺害的母親克呂泰墨斯特拉和一個作為祭品而被犧牲掉的女兒伊菲革涅亞。”跟伊菲革涅亞們不同,安吉拉們不再甘心成為男人書寫的對像,她要為自己書寫,她要親口講述自己被人玷污的那個羞恥,她還原諒了作為父權法律幫兇的母親。同樣地,阿裡阿德涅們勇闖法律迷宮,直視彌諾陶洛斯,這回害怕的卻是彌諾陶洛斯,“卷縮進他的殼裡,冷冰冰地,像隻蝸牛”。 當安吉拉向巴亞多講述她的她史的時候,弱者的名字便成了男人,“整個社會開始營救受傷的那一方:即悲痛欲絕的男人”。覺悟後的女人們“打碎了詞語的脊梁”,用自己的書寫和回視來反抗家長制和法律暴力,提醒法律尊重他異性,敦促法律還給女人所有的虧欠,因為“一個女人就是所有的男人”。
《法律與文學:從她走向永恆》對於法律文學研究的參考價值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1) 文學是法律的基石。西方傳統法律思想在希臘神話中得到充分的論述,謀殺—復仇—正義聲張是西方法律的因果循環,謀殺的動因在於滿足行兇者自己的欲望,亂倫禁忌是建造法律迷宮的主要驅動力。
(2) 法律無法解決法律意欲解決的問題。法律控制欲望的企圖在謀殺—復仇這個父權法律迷宮中難以得逞,法律本身也是欲望,是控制欲望的欲望,是男人對生育能力欲望的一種替代性表達方式,法律其實也是一種模仿,盡管它害怕模仿、差異性和女人,破解謀殺—復仇這個報應循環的出路在於另外的語言和另外的法律,特別是女性的語言和女性的法律,一種用“身體”和“感觀”打碎了“詞語的脊梁”之後所書寫的愛的語言和法律。
(3) 女人的存在不能隻為父權法律而正名,女人應該建立自己的法律。女人是父權法律的犧牲品、交易對像和幫兇,女人一開始就是男人的附屬品,夏娃是從亞當身上一個肋骨造出來的,雅典娜是從她父親宙斯頭顱裡出生的。母親,是每個人的“第一個家、第一個身體、第一個愛”,然而母親有時候實際上又有意無意地扮演了家長制和法律暴力的幫兇,在安吉拉無法“在自家庭院晾曬污跡斑斑的亞麻床單”從而玷污了維卡略家族的榮譽之後,最想活埋安吉拉的卻是她的母親。安吉拉的寫作和阿裡阿德涅的回視都是在掙脫父權法律的桎梏從而開始建立另類法律:她們建立的“不是法律而是愛,不是死亡而是永恆,不是責任而是美好事物”。
(4) 文學的幻想是法律的理性在認識世界時的必要補充。宇宙萬物無外乎能量、信息和物質,波動定律認為,所有的物質現像都是波動的,萬物不同,皆因頻率不一。文學作品認識世界的觀點和角度跟現代量子力學很接近:那個“阿萊夫”雖小卻包含了整個宇宙,這個“阿萊夫”就是一粒小光子,就是量子;人人都想得到兩毛五硬幣“扎希爾”(the Zahir),因為在這個硬幣的背後可以發現上帝,這就無須像《神秘奇跡》中死囚犯那樣隻有在臨死前的禱告中纔聽見上帝的回答;虛構的特隆星球(Tlon)甚至會入侵地球;《圓形廢墟》中主人公可以通過做夢“夢出了一個兒子”,或許我們每個人“都是別人夢中的人”。地球與“扎希爾”究竟哪個是夢,哪個是現實?一切法從心想生,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境由心轉,相由心生。宇宙的真相就是那一念,就是幻想。
(5) 真相在立場和情緒面前已不重要。在發生了那樁事先張揚出去的兇殺案之後,小鎮居民對當時天氣的回憶都相互矛盾,那麼,那些親歷者對於這場兇殺案的證言又有多少可信度?小鎮居民爭相講述所謂的事實與其說在揭示真相倒不如說是在表達自己的立場、看法和情緒,真相不可得,“凡有所相,皆為虛妄”。一念迷,念念迷;一念覺,念念覺。法律注重規範性,而文學注重解釋性、差異性和多樣性。法律講究證據,文學講究情理。法律迷宮裡的真相就是彌諾陶洛斯,彌諾陶洛斯也許本就不存在,“一切法無所有,畢竟空,不可得。”法律在詹姆斯一世看來“是規定道德品行和社會生活的規則,而不是誘捕良民的圈套:因此,法律必須根據法律意義而不是文字本義來解釋”。
《法律與文學:從她走向永恆》是法律、文學以及法律文學愛好者的良師益友。筆者在翻譯此書的過程中不斷停下來查閱有關量子力學、佛學經典、犯罪心理學等有關認知、意識和世界觀的前輩所思考的智慧結晶,深感受益匪淺,非常感謝《法律與文學:從她走向永恆》英文原著豐富的啟智性的語言和思想,非常感謝華東政法大學外語學院對這個中譯本出版的支持,非常感謝我的家人特別是家裡的女人們給予我的愛,感謝父母任勞任怨照顧全家飲食起居,感謝妻子一直以來給予我的分擔和鼓勵。此刻透過窗外灰蒙蒙的天空直視月亮般的太陽,一股強烈的衝動想把那些寫滿凌亂詞語的草稿撕碎扔掉陪女兒出去尋找一片藍天,哪怕藍天下的陽光強烈不可視,“爸爸,你什麼時候可以做完作業陪我玩”,“寶貝,現在就可以”。
薛朝鳳2017年1月1日於集英樓 查看全部↓
" | | |
| | | | |
|




